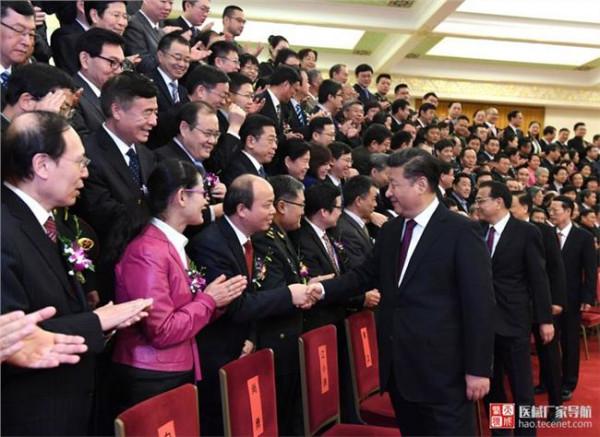林文月连战 连战表姐林文月:大家闺秀冲淡为文
林文月说:她不习惯接受媒体面对面的采访,仅有的几次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尽管如此,当她近日与家人踏上申城寻根,适得新作《三月曝书》出版方邀请,在季风书园的走廊书吧坐定,面对记者的频频发问,依然保持了亲切随和、镇定自若的风度。
问到感兴趣的话题,这位以散文、学术、翻译“三笔”风靡中国台湾地区的知名学人,会用略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一如她的散文,平淡、自然、有回味。不便言及什么,她就淡淡地回避开,在恰如其分中透露出她的人生态度:远离喧嚣和浮躁,但求岁月静好。
尽管已届七旬,眼前的她却看不出年纪,略加修饰的眉是平和舒展的,一身咖啡色的上衣是熨帖的,眼神安静、柔和,带着阅尽人世沧桑之后的纯然和志趣,却不禁让人想到她背后的人生故事。
林文月1933年出生于上海日租界。外祖父是有“台湾太史公”之称的连横,表弟是连战。父亲林伯奏是台湾彰化县北斗镇人,早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奖学金赴上海,进入日本人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上海分校,毕业后在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上海支店任职,并从事房地产生意,在上海虹口一带有不少房产,林文月就是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十多年,而她曾因被店主善待而念念不忘的家边小书店,据众多学者考证,正是著名的内山书店。
在日本占领台湾的年代里,依据《马关条约》,台湾地区居民都是日本国籍。小学五年级以前,林文月一直在上海接受日式教育,由于年龄尚小,父母也就没有给她讲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的历史,她“一直把自己当日本小孩”。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战败那天,在小学操场上,她跟日本同学一起哭,“以为自己是战败国的子弟,过两天,才发现自己是战胜国的公民”。
所以,在林文月的回忆里,小时候的身份一直是不定的。“我的母语其实是日语,我最先会讲的是日本话,在家还会说点上海话。回到台湾,我不会讲台湾话,国语也不会。但对我来说,讲日本话最方便,突然之间就要改变我的生活和习惯。所以,最初在台湾上学时,我用不熟悉的台湾话来解释我更不熟悉的国语。后来才慢慢习惯。”
那时的她自然想不到,正是这样复杂的身份,使得她可以比较客观地看事情并作评价,日式学堂的启蒙教育,也为她日后翻译《源氏物语》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林文月透露,自己走上翻译道路,纯粹出自一场歪打正着:1969-1970年,她远赴京都大学留学一年,专攻比较文学,论文题目就是“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其中她提出:没有《长恨歌》,就没有《源氏物语》,“可能很多国人都不知道,这部日本最伟大的名著是受到白居易《长恨歌》影响,故事开始就引用了《长恨歌》中的语句,把桐壶天皇对桐壶更衣的宠幸比作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关系。”
当时《源氏物语》还没有中文译本出版,为了让读者了解论文,林文月试着把第一章翻译出来,附在论文后。论文还未受到关注,这篇附录横空出世,引发了出版社的浓厚兴趣,希望她继续翻译整部作品:“天,他们不知道后面还有54章!”但喜欢“踮起脚做事”的林文月抱着姑且试之的心态,在《中外文学月刊》上开始翻译连载,花了5年半时间,总共有1300多页,100万字,“感觉像跟时间跑马拉松赛”。
很多年后,林文月才知道,在她翻译之前,丰子恺就已完成了翻译,但译本的出版却在她之后:“很可惜,如果能够早点看到,也许能从中学习到很多。”但同时她也庆幸,“如果知道丰先生已经翻译了,我怎么敢翻译呢?而且那样的话,我遇到困难,就会很依赖地去参考他的文字,也可能保留了丰先生译得不妥之处。”
也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林文月开始散文写作。她回忆说:当时,我顺带给台湾一个文学杂志写文章。但那个杂志主编对我说:“文月,你干嘛写那些正经八百的文章,写一些有趣的东西。”我说:“要写什么?”他说:“随便你,每个月写一篇”。林文月就陆续写了京都生活的散文,后来收集在《京都一年》中,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来把京都生活、文化介绍给台湾人,当时能出国的台湾人还是很少的。
关于林文月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名门子弟”这个标签。对此,她十分坦然:“外祖父去世时我才三四岁,但已经是第三代中唯一有与他老人家合影的。我母亲是长女,连震东是外祖父的独子,连战是连氏二度单传。我与弟妹先后有四人入台大,包括学政治学的连战,只有我是中文系。”得知林文月考入台大中文系,舅舅曾竖起大拇指,称“外祖父的文学遗志有此女承继了”。
这位承继外祖父“文学遗志”的大家闺秀,却写出了在众老饕心目中堪比袁枚《随园食单》的《饮膳札记》。谈及这个话题,林文月兴趣盎然。她说:袁枚是遣家中厨师四处学艺,我则是亲身尝试,台静农先生、许世瑛先生、董桥、林海音、三毛,都曾在饭桌上捧过场。
学生笑我做菜像做学问,记了许多笔记。“其实,最开始我是为了避免重复以同样的菜式款待同样的客人,才用卡片记录每回宴请的日期、菜单,以及客人的名字,而今再度翻起,许多师长已经故世,许多朋友已经离散,更是唏嘘。”
出生于名门之家,一身兼做学术、翻译和文章,又不失烟火气息,林文月是女性心目中的“得天独厚”,多年前她写到:我实在不佩服现在那些只知道写论文,从不敢进厨房的女教授。人生岂不就是苦乐参半?一个女性教员和家庭主妇有甘有苦,实在也是应该的。而今,冲淡许多的她选择更有意味的另一说法:“我觉得我必须要先做一个人,再做一个女人,再做一个学者、作者或者是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