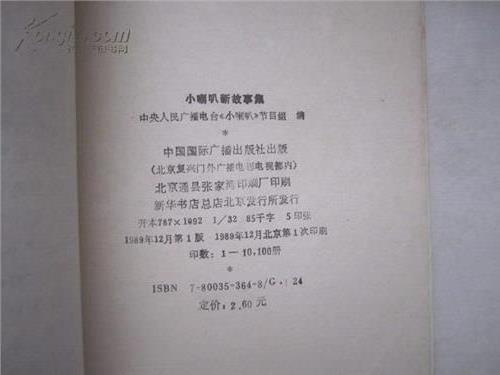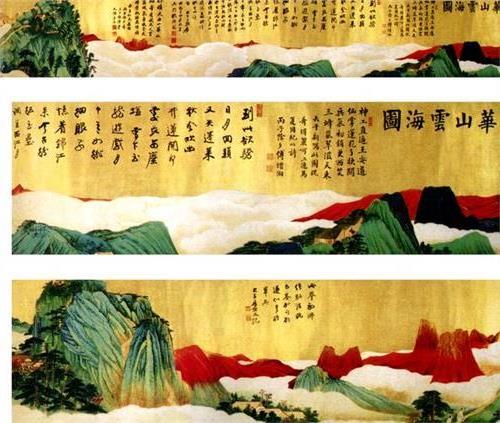齐天乐的意思 姜夔《齐天乐》鉴赏
姜夔有《齐天乐》一词吟咏蟋蟀,词有小序,兹并录如下:
丙辰岁,与张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辞甚美。予徘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寻亦得此。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一寄托主旨及其原因
首先分析其寄托主旨,历代词话对其词旨已有详细论述,如: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白石《齐天乐》一阕,全篇皆写怨情。”宋宋翔凤《乐府余论》说得更具体:“(白石)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

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则辞愈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无论是前者笼统概述的“怨情”,还是后者具体的“伤二帝北狩”,都包含着幽怨凄凉的感情色彩。胡云翼先生认为此词“大约是自伤身世之感”,但“究竟作者有何寄托,实在是难以捉摸”。我认为这寄托还是有迹可寻的。不仅是与其时世遭遇密切相关,而且是作者悲苦心境的投影使然。

首先,姜夔生当一个令人灰心失望的时代。据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记载,白石一生经历南宋高、孝、光、宁四个朝代,在他二十至五十岁期间,正值宋、金议和、南宋偏安,在这三十年“承平”日子里,朝野荒漠,国耻国仇置于度外。
白石二、三十岁时,数度客游扬州、合肥及江、淮之间,是属边区。符离战后,其地生产凋敝,风物荒凉,于是引起词人“徘徊望神州,沉叹英雄寡”(《昔游诗》)的感慨。《扬州慢》、《凄凉犯》一类词也颇有“黍离之悲”。
再次,从姜夔的生平际遇来看,他一生过着浪迹江湖、寄人篱下的生活。青年时,曾北游淮楚,南历潇湘,后客居合肥、湖州和杭州。除了以卖字为生之外,大部分是靠别人的周济生活。这种终生客居他乡的生活,让词人体会到一种漂泊感和孤独感。
这里的“漂泊”不仅是指生活方式,更是指心灵体验;这里的“孤独”不仅是形影相吊,更是精神归属感的消失。因此他常常感叹“客途今倦矣”(《徵招》),有着“飘零客,泪沾衣”(《江梅引》)的惆怅,“流光过隙,叹杏梁双燕如客”(《霓裳中序第一》)的愁情,“奈楚客,淹留久,砧声带愁去”(《法曲献仙音》)的凄凉。
再次,姜夔一生怀才不遇,终身布衣。对中国文人来说,“遇”与“不遇”的生活遭际,对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反映在文风上是迥异其趣的富丽与清冷。同样的精心刻镂、音律和谐、词风婉约的周邦彦词之所以与姜词的清冷孤峭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富丽精工的风格,也正因为周邦彦几乎一生为官,甚至官到“提举大晟府” 这样国家音乐机构主管的职务,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心境平和雅正,词的风格自然趋于富丽堂皇。
而姜夔一生贫病交加,长期受助于张鉴,张鉴死后,他生计每况愈下,但仍清贫自守,不肯屈节以求官禄。他的友人苏洞曾说:“白石鄱姜病更贫,几年白下往来频。歌词剪就能哀怨,未必刘郎是后身。”
山河破碎,世道坎坷,浪迹江湖,寄人篱下,怀才不遇,贫病交加,种种原因,使得姜夔对凄凉寒苦有着深刻的感受,所以他总是以一种忧郁、凄凉、愁苦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即《卜算子》中 所说的“举目悲风景”。心理的凄凉投射到客观物象上,产生的文学风格必然带有幽怨清冷色彩。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论“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 可谓深中肯綮之言。
二“蟋蟀”的文化意象内涵
从词序中可看出,姜夔与张功父作词的缘起是“闻屋壁间蟋蟀有声”。为何蟋蟀能成为情感的触发点,使词人选择它作为吟咏的对象,以发悲秋之幽情?这与“蟋蟀”作为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一个蕴涵深远的文化意象是分不开的。蟋蟀鸣而天下知秋,而“悲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表现得最多、最丰富的情感,文人们似乎都很偏爱“悲秋”这种情绪。
中国古代文学表现“悲秋”始于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种感伤情绪一进入楚辞就带上了文人特有的忧患和失落。“蟋蟀”与其存在的季节秋天紧密相连,因此“悲秋”现象使得古代吟颂蟋蟀的诗人大多无法摆脱这一审美移情心理。“蟋蟀”的文化意象内涵具体来说包含以下三种:
第一.人生失意的忧愤痛苦。如宋代史达祖《秋霁》中的“露蛩悲、清灯冷屋,翻书愁上鬓毛白”两句,把孤独惆怅之情、江湖流落之感、怀才不遇的悲凉借蟋蟀意象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很多诗词中,蟋蟀都有类似的愁苦意象特点。
如“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音响一何悲,弦急如柱促”(《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白居易的“闻蛩唧唧夜绵绵,况是秋阴欲雨天。犹恐愁人暂得睡,声声移近卧床前”(《促织》) ;杨万里的“一声能遣一人愁,促织声声晓不休”,“人生如何无苦乐,一般蟋蟀两般愁”(《蛩声三首》) 。
第二.离愁和相思。如宋代李清照《行香子七夕》:“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词人抓住秋天自然现象的两个突出特征落笔。蟋蟀在草丛中幽凄地鸣叫着,梢头的梧桐叶似被这蛩鸣之声所惊而飘摇落下,突出整首词的核心---“愁”,此刻的悲秋情怀是同牵牛织女一样的离愁别恨。再如唐人雍裕之《秋蛩》:“鸣蛩谁不怨,况是正离怀。”借“蟋蟀”抒离别之情。
第三.怀乡之思。唐人杜甫的“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促织》) ,是借咏蟋蟀的哀音来抒写久客在外的愁思。清人陈澧《齐天乐》:“倦游谙尽江湖味,孤蓬又眠秋雨。……乡梦更无寻。幽蛩不语……归期又误”,蕴含了深重的思乡之情。
三《齐天乐》赏析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庾郎”,即庾信,曾作《愁赋》,今已不传,但据姜夔《霓裳中序第一》“乱蛩吟壁。动庾信,清愁似织”来看, 《愁赋》大约与蟋蟀有关(蛩是蟋蟀的又一别称),即使无关,顾名思义,也可以想见是哀愁之作。
庾信本在南朝任官,素有文名,后出使西魏,从此羁留北朝,不得南归,虽位高名显但思念故国,作《哀江南赋》以哀痛梁朝的灭亡。杜甫诗云:“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而姜夔作此词时,正是1196年,北宋已倾覆七十年,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不思进取,也难逃灭亡命运。
姜夔之愁与庾信之愁通过“蟋蟀”这种情感的载体,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对应。这种愁,绝不是简单的文人悲秋,而是家国之愁,是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的士大夫之悲。
“私语”即蟋蟀凄切细碎的声音,晚秋时候的蟋蟀声常时断时续,略带颤音的鸣声变得有气无力,给人如泣如诉之感,难免不让人愁绪万千。宋代贺铸在《天香》中写到:“烛映帘栊,蛩催机杼,共苦清秋风露”,极言秋日黄昏,伴着蛩鸣,所产生的无尽的 “天涯倦客”的愁思。“更闻”与“先自”相呼应,吟赋悲声与悲戚虫声交织在一起,寄寓了词人深沉的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
“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铜铺”指铜做的铺首,装在门上衔门环,此指门外。“石井”,此指井栏边。这里点明了蟋蟀生长的地方,大多是环境湿冷的地方,渲染上了一层清冷的色彩。其中“侵”字,炼字传神,形象写出了青苔铺满井栏的画面,类似的用法有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远芳侵古道”。
“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哀音似诉”,承上“私语”而来,这如泣似诉的声声哀鸣,使一位本来就辗转无眠的思妇更加难以入梦,只有起床以织布来排遣烦忧。在思妇诗词中,“蟋蟀”是经常出现的意象。例如,敦煌曲子词《菩萨蛮》:“香销罗幌堪魂断,唯闻蟋蟀吟相伴。
每岁送寒衣,到头归不归?” 南北朝谢眺也有“秋夜促织鸣,南邻捣衣急。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伫立。”此类诗词中,描写的都是月凉夜静的晚上,思妇辗转难眠 ,充耳的是唧唧的蟋蟀鸣声,声音时缓时急,时大时小,像风吹落叶,萧然惊心,引发的是绵绵的愁绪。
轻吟之下,独守空房的思妇会更加思念漂泊远方的丈夫而觉孤苦。“起寻机杼”是一个无意识的动作,类似于李清照《声声慢》开头中所描述“寻寻觅觅”,思妇百无聊赖,若有所失,于是东张西望,总想做点什么事情来消解自己的孤独寂寞。
“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依然是写思妇怀念征人的心情。面对屏风上的远水遥山,不由思绪万千。
“甚情绪”实际包含了千愁万绪:何时才能将亲手织就的冬衣送到远方征人的手中?秋夜露寒,什么时候征人才能回到自己的身边?远人遥隔,而此时只余一人对影自怜,又有什么情绪来排遣忧愁呢?几句言简意远,委婉尽情。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首句岭断云连,最得换头妙谛,被后人奉为典范。“岭断”指其空间和人事的更换,“云连”,指其做到境换意连,脉络暗通。在这句中,由室内的思妇转到室外的捣衣女,但两者之间的情意是相通的,思妇无眠,寄托的是思念,女子捣衣,同样蕴含着此种情怀。
秋风萧瑟,天气转凉,该添置寒意,特别是当亲人远离自己时,织布缝衣就更寄托无限情意,如李白《子夜吴歌》: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何时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同时此句中“暗雨”这个意象也值得注意。一方面,此意象代表了白石词一贯的清冷风格,词人偏爱冷香、冷红、冷月、冷枫,暗柳,暗雨等衰落、枯败、阴冷的意象,形成一个“清冷意象群”,以此构造幽冷悲凉的词境。另一方面,细细密密、潺潺不断的雨,也正是思妇和捣衣女无处不在的愁情的象征,本就彻夜难眠,又遇阴沉雨天,正是“夜长衾枕寒”,听着雨滴“空阶滴到明”。
“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此句继续写蟋蟀鸣声的转移,将空间和人事推得更远更广。“候馆”可以包含迁客骚人,游子征人等;“离宫”,可以包括不幸的帝王后妃、宫婢彩女。这些飘泊者、失意者,不论尊卑长幼,都要悲秋吊月,闻虫鸣而无限感伤,个人不幸或家国之痛萦绕心头。直到今天,蟋蟀的哀鸣声依然回荡在游子的耳旁,萦绕在诗词的字里行间。如:现代台湾诗人洛夫《蟋蟀之歌》,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
“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豳诗漫与”,词人说自己受到蟋蟀声的感染而率意为诗了,此语出自《诗经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但下面突然插入“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两句,写小儿女呼灯捕捉蟋蟀的充满乐趣的画面,声情骤变,与前面的悲伤情调似乎很不符合,但这种以喜衬悲而欲觉悲的写法,比直接描写更感人至深。
例如李清照《蝶恋花》“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眉腮,已觉春心动”来写心情的喜悦,接着又以“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市”来写诗情酒意没人相伴而引起悲伤落泪。
正如陈廷焯所说:“以无知儿女之乐,反衬出有心人之苦,最为入妙。”(《白雨斋词话》)以乐笔写愁然,正是白石词的匠心妙用。这种天真儿女所特具的乐趣,反衬原本就无限幽怨凄楚的琴音,使其变得“一声声更苦”了。
整首词遗貌取神,离影得似,从虚处着笔,写蟋蟀,却不局限于蟋蟀,即叶嘉莹所说“是要摄取事物的神理而遗其外貌”(《灵溪词说》),从蟋蟀的哀鸣转到听哀鸣的人,妙在如“野云孤云,去留无迹”(张炎《词论》)。古来写蟋蟀诗词甚多,唯白石写来清空。
正如许昂霄《词综偶评》所言:“将蟋蟀与听蟋蟀者,层层夹写,如环无端,其化工之笔矣。” 《唐宋词一百首》也评点:“蟋蟀本无甚可写,所以词中着力刻画蟋蟀鸣声和听其鸣声的人,将二者层层夹写,多从侧面着笔,顿显灵动,咏物而不粘着于物,方成咏物高境。”
参考书目:
【1】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
【2】唐圭璋《唐宋词鉴赏辞典 南宋辽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3】王洪《唐宋词精华分卷》,北京:朝华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