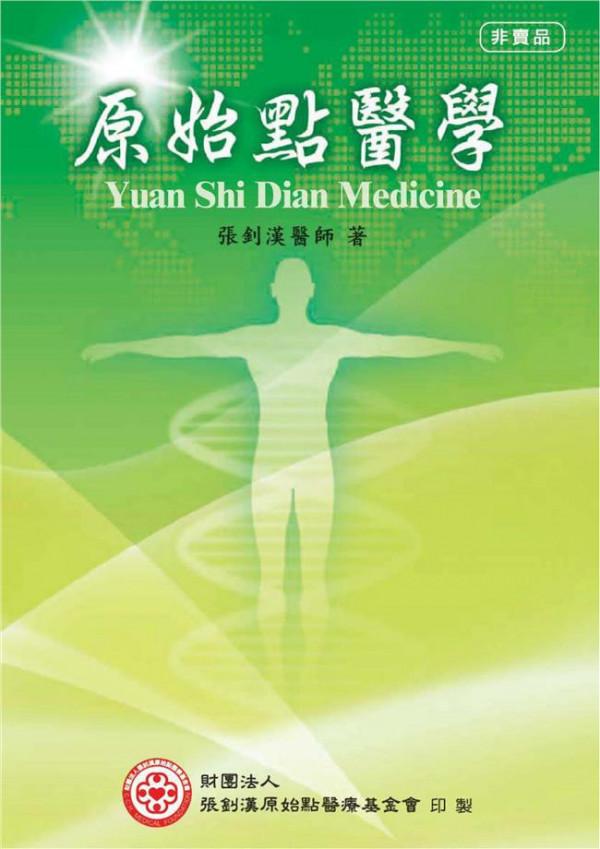【邵雍击壤集】刘春雷: 从《击壤集》看邵雍的身体意识
《伊川击壤集》(以下简称《击壤集》)是北宋大儒邵雍的诗歌总集。与哲学巨制《皇极经世》相比较,《击壤集》中的诗歌创作在邵雍整个著述活动中无疑居于次要地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宋人晁公武《读书志》说:“雍邃于易数,歌诗盖其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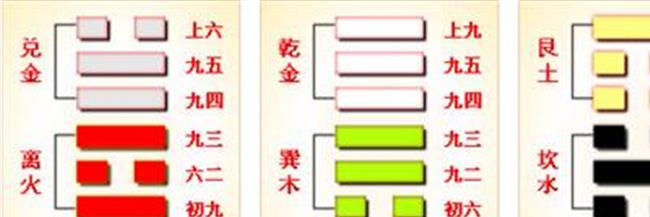
”《四部丛刊》辑《康节先生伊川击壤集后序》也指出:“其发为文章者,盖特先生之遗余。至其形于咏歌声而成诗者,则又其文章之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诗歌创作的次要地位是相对于邵雍的道德境界和哲学创制而言,这并不能掩盖《击壤集》的思想价值及其对理解邵雍其人其学的独特意义。

诗集“第一现场”式地保留了邵雍大量的日常生活体验,呈现了在生、老、病、死等生存境遇下丰富多彩的身体样态,展现了邵雍哲学创制中鲜明的身体意识,以及在穷究天人之际之后面对生、老、病、死等人生问题时的真知灼见和旷达情怀。

一、生之喜悦:康泰身体的怡然舒展
“生、老、病、死”是人们谈论人生在世整体结构的常用语,展示的是生命过程的不同阶段和境况。生命的有限性首先表现在肉体生命的有限性。肉身生命的生、老、病、死既是生命无可逃避的宿命,也是人作为此在的基本生存境遇。作为经验性情感,喜、怒、哀、乐与人的肉体感官直接相关,与人的生、老、病、死共同构成人生在世的基本生存样态。
邵雍认为,人的身体“合天地而生”,是仿效天地大宇宙、与其同构一体息息相关的小宇宙。就人的存在而言,其整体生命之畅达、宇宙精神之通泰,首先要落实到肉身躯体之健全、器官机能之有效、基本生理需求之满足和感性欲望之实现。
邵雍有许多文字描写“安乐”之身和“肉身之乐”,表面属于基本生理欲望,实则关涉宇宙之通泰、生命之应然:“六尺眼前安乐身,四时争忍负佳辰。……量力杯盘随草具,开怀语笑任天真。”(《闲适吟》)“身老太平间,身闲心更闲。
非贵亦非贱,不饥兼不寒。有宾须置酒,无日不开颜。”(《年老吟》)“老年躯体索温存,安乐窝中别有春。万事去心闲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林下五吟》其一)“行年六十一,筋骸未甚老。
已为两世人,便化岂为夭。况且粗康强,又复无忧扰。如何不喜欢,佳辰自不少。”(《欢喜吟》)“行年六十二康强,况复身居永熟乡。美景良辰非易得,浅斟低唱又何妨。无涯岁月难拘管,有限筋骸莫毁伤。”(《六十二吟》)在邵雍的世界里,个人的“六尺之身”、“康健”“筋骸”感通着“四时”“佳辰”“良辰美景”,体证着小范围的“安乐窝”“永熟乡”、大范围的“两世太平”“四朝全盛”。
邵雍本人通过健全的躯体随自然大化自由舒展,并与整个社会人生达成一体的共在。
良好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标志。邵雍认为失眠是身心机体正常功能的紊乱,往往根于大惊、大忧、大伤、大病、大悲、大喜,实质是受外物俗情羁绊、不能超脱达观所致,他说:“大惊不寐,大忧不寐,大伤不寐,大病不寐,大喜不寐。
大安能寐。何故不寐?湛于有累。何故能寐?行于无事。”(《能寐吟》)邵雍本人以能酣睡安眠为福气,字里行间流露欣然自得的愉悦:“一瓦清泉来竹下,两竿红日上松梢。窝中睡起窝前坐,安得闲辞解客嘲。”(《自乐吟》)一夜酣然是如此,白昼小睡也是难得的乐事:“昼睡工夫未易偕,羲皇以上合安排。
心间无事饱食后,园里有时闲步回。未午庭柯莺履啭,已残花径客稀来。请观世上多愁者,枕簟虽凉无此怀。”(《昼睡》)在邵雍看来,睡眠不单单是肉身自我调整的生理现象,也和人的心理、情绪、精神状态息息相关。
对身处繁杂世事中的“社会人”来说,只有凭借后天的工夫和修养,消解俗事物累对心灵的羁绊,才能重新敞亮自由的先天之心并进而放松肉身、酣然入眠。
在邵雍笔下,“昼睡工夫未易偕”,需要“心间无事”,需要“饱食后”“园中闲步”回来,需要树上鸟鸣婉转、园中花径无人……这是“天造地设”的自然情形,又是超然物外的主体境界,只有在这种状态,才能做到“大安能寐”,身心才能真正放松、休憩。
身体的康泰、生命的舒展,往往意味着心情的愉悦、生命的欢欣,这些又在身体器官上油然呈现。邵雍在诗中多次描写“眉”“眼”的细节,生动刻画了一位安贫乐道者肉身生命的舒展和精神世界的超然高蹈:“男子雄图存舍用,不开眉笑待何时”(《和人放怀》),“人间好景皆输眼,世上闲愁不到眉”(《清风短吟》)。
与其他儒者一样,青年邵雍怀有修齐治平的伟大志向和抱负,宋史记载,“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成年后的邵雍并未走上传统儒家外在事功的人生道路,而是在另一路径上开拓出儒者新的生命境界,这是在宋代理学背景下的卓越贡献。
在邵雍的世界里,外在的事功并不构成人生价值的唯一或必要条件,功名事业的成就与否、人生际遇的穷通舍用,都不是阻碍生命舒展的理由;在理学的时代大语境下,邵雍以自己的思和诗、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拓展了儒者新的生命场域,诠释出儒家“内圣外王”的新意蕴,为儒者提供了另外一种新“活法”。
这种新“活法”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智慧,既有老庄道家少私寡欲顺应自然的物化逍遥,也有儒家安贫乐道式的孔颜之乐。
邵雍诗歌还有多处描写精神洒脱状态下“眉”与“眼”的自在舒展,借以展示整体身心的依然自在:“脱屣风波地,开怀松桂秋。
两眉从此后,应不着闲愁。”(《代书寄祖龙图》)“无怨可低眉,有欢能抵掌。”(《代书戏祖龙图》) “天下太平日,人生安乐时。更逢花烂漫,争忍不开眉?”(《太平吟》)“几何能得鬓如丝,安用区区镊白髭。……多少宽平好田地,山翁方始会开眉。
”(《喜老吟》)以“眉”“眼”为代表的身体器官之所以不舒展、不自在,源于主体之身或主体之心有太多的牵挂与物累。不同于禁欲主义者借由约束肉身欲望而实现精神的自由升华,儒家在尊重肉身正常生理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精神的自由和愉悦;对邵雍而言,拒绝过多的欲望和追求依然是身心自由之必需。
因为心中没有挂碍,所以“眉”上不着闲愁、不着怨愤,而是在眉眼的舒展中流露生命的愉悦和欢欣。这种情感的欢愉具体表现为身体器官的舒展、解放,正是生命本身也是宇宙生机的活泼发用。
二、老之安然:衰老身体的乐天顺化
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一切生物体的活动都伴随着器官功能的盛极而衰、逐渐退化、丧失,在生存论意义上这就是所谓“必死的时间性”。衰老以及作为衰老必然结果的死亡是完整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人生无可逃避的宿命,并因此成为古今哲人孜孜探究的永恒话题。
邵雍享年六十七岁,早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对自己身体机能老化衰退有清醒的意识,在诗歌中多次提及“年老”“白头”“脱发”“齿衰”等衰老表现以及这些衰老之象对精神的冲击。
嘉佑元年即公元1056年,邵雍四十六岁,他在诗中写道:“及正四十六,老去耻无才。残腊方回详,新春又起灰。非唯忘利禄,况复外形骸。白发已过半,光阴任自催。”(《依韵和张元伯职才岁除》)“百病筋骸一老身,白头今日愧因循。
”(《问人丐酒》)“草绿露沾衣,草衰风切肌。……有齿日益衰,有发日益脱。获罪固已多,此心难屑屑。”(《秋怀三十六首》其一)面对“逝者如斯”的时光飞逝以及肉身无常、不觉老去的生命现实,邵雍也难免有物是人非、人生如梦的感叹:“当年曾任青春客,今日重来白雪翁。
今日当年已一世,几多兴替在其中。”(《和张二少卿文再到洛阳》)“正当老辈过从日,况值高秋摇落天。一把黄花一罇酒,故人西去又经年。”(《又一绝》)生命机能的衰退老化,应是一切正常生命体都有的生命感触,也成为很多人共通的人生感慨。
然而,邵雍是以高明的易学智慧来看待自身的衰老,清醒地认识到衰老与生长、壮大一样都是生命发展的正常过程,是生生不息易道循环的展现形态。因此,邵雍笔下的衰老之态没有哀伤之情,而是充满生机、活力和欢乐:“行年六十有三岁,二十五年居洛阳。
林静城中得山景,池平坐上见江乡。赏花长被杯盘苦,爱月履为风露伤。看了太平无限好,此身老去又何妨。”(《老去吟》)“凌晨览照见皤然,自喜皤然一叟仙。慷慨敢开天下口,分明高道世间言。
虽然天下本无事,不奈世间长有贤。自问此身何所用,此身唯称老林泉。”(《览照吟》)“身老太平间,身闲心更闲。非贵亦非贱,不饥兼不寒。有宾须置酒,无日不开颜。第一条平路,何人伴往还?”(《年老吟》)“前有亿万年,后有亿万世。
中间一百年,做得几何事?又况人之寿,几人能百岁?如何不喜欢,强自生憔悴。”(《人生一世吟》)面对身体机能的老化,邵雍之所以“开颜”“欢喜”,并不在于“衰老”这个事件本身,而是他看到身体小宇宙背后的天地大宇宙、小生命背后的大生命。
在邵雍看来,“衰老”并不是一己身体孤独地老去或者个体生命逐渐丧失,而是小宇宙与大宇宙、小生命与大生命在时间的洪流中一体共在、流动变迁的具体形态。基于易学家洞彻亿万年的易学智慧,审视不过百年的肉身生命,“身老于林泉”“身老太平间”,确乎是实现了肉身生命活泼自然的应然价值。
对生命整体而言,衰老并不完全是消极的。随着肉身器官衰老退化,人的智性和精神往往不断进步、成熟;因此从经验积累和生命自觉的角度看,衰老又具有积极价值。经历更多岁月磨砺,邵雍对世界、人生、自身和生生不息的易道精神有新的体验和更深刻的领悟。
只有智性足够成熟、人生体验足够深刻、阅历足够丰富,才能超脱世俗人事、功利荣辱:“齿发既衰非少日,林泉能老是长春。行于无事人知否,宠辱何由得到身。”(《进退吟》)岁月磨砺催老了身躯,却增长了涉世安身的智性功夫:“筋骸得似当年否,气血能如旧日无。
却喜一般增长处,罇前谈笑有功夫”(《答人吟》),陶冶出豁然开朗的人生态度:“今年花似昔年开,今日人开昔日怀。烦恼全无半掐子,喜欢常有百来车。
光阴已过意未过,齿发虽颓志未颓。人问尧夫曾出否,答云方自洞天来。”(《对花吟》)他在天人之际辨分别、“自诚明”,进而“通天地”、“了生死”:“天生此身人力寄,人力尽兮天数至。天人相去不毫芒,若有毫芒却成二。
”(《人吟》)“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向其间一事,须是自诚明。”(《逍遥吟》)另外两首诗也集中记述邵雍在身体衰老的感知中体悟到生命的真谛:“它山有石能攻玉,玉未全成老已催。有限光阴随事去,无涯衰朽逐人来。
陶镕情性诗千首,夑理筋骸酒一杯。六十六年无事日,心源方始似昭回。”(《书事吟》)“风吹木叶不吹根,慎勿将根苦自陈。……万水千山行已遍,归来认得自家身。”(《风吹木叶吟》)从某种意义上说,衰老是生命个体的“去生命化”,既是生命现象,也是“逆生命现象”。正是在这个“去生命化”的“逆生命现象”中,邵雍完成了对生命本真的领悟。
三、病之坦然:病疼身体的超然达观
根据《宋史》记载,邵雍身体并不强健。他思穷造化、学究天人,一生沉浸在建构以《皇极经世》为代表的庞大象数易学体系著述活动,虽然自号“安乐先生”,但殚精竭虑之后,一直深受类似神经衰弱的“头风之疾”的折磨,以至于“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以帷遮之,密不透风。
躯体的病痛、器官的病变能够强烈提醒人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邵雍有大量诗篇描写自身疾病和身体遭受的痛苦:“近来多病不堪言,长欲醺醺带醉眠。
…… 自知命薄临头上,不愿事多来眼前。”(《重阳前一日作》)“烦疴熸躯体,溽暑烁楼台”(《别谢君实端明》)另有《臂痛吟》:“先苦头风已病躯,新添臂痛又何如”,《头风吟》:“近日头风不奈何”,《病起吟》:“病作因循一月前,岂期为苦稍淹延。
朝昏饮食是难进,躯体虚羸不可言。”《有病吟》:“身之有病,当求药医。药之非良,其身必亏。”《重病吟》:“安乐五十年,一旦感重疾。仍在盛夏中,伏枕几百日,砭灸与药饵,百疗効无一。”
邵雍对待疾病的态度,首先是对症下药、积极医治。邵雍指出,“身之有病,当求药医。药之非良,其身必亏。”(《有病吟》)“一身如一国,有病当求医。病愈药便正,节宣良得宜。”(《有病吟》)然而,躯体的病变因躯体的存在而存在,比有限的肉身更加有限;病痛问题的最终解决并不能在躯体本身实现,而是要诉诸于心的觉悟尤其是对生命整体的了悟。
在精通易学、深识造化之几的邵雍看来,病痛是与生长、衰老等现象一样自然的生命现象。
人作为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可以实现对有限的肉身病痛的超脱。面对身体的病痛,邵雍的态度是超脱豁达的,处处洋溢着乐天命、顺自然的精神。在一年轮回的新春开始,邵雍表达了超越多病身躯的“不动心”功夫,《新春吟》曰:“多病筋骸五十二,新春犹得共衔杯。
践形有说常希孟,乐内无功可比回。燕去燕来徒自苦,花开花谢漫相催。此心不为人休戚,二十年来已若灰。”邵雍诗歌多次写到对待病痛“顺天”的态度:“安乐窝中设不安,略行汤剂自能痊。
居常无病不服药,就使有灾宜俟天。”(《安乐窝中吟》其一)面对头风病痛,“汤济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答客问病》)面对臂痛:“无妨把盏只妨拜,虽废梳头未废书。不向医方求效验,唯将谈笑且消除。大凡物老须生病,人老何由不病乎?”(《臂痛吟》)即使是病沉难治,也是“以命听于天,于心何所失。”(《重病吟》)
面对身体的疾病和痛楚,邵雍不仅能乐天安处,而且超越病痛之苦焕发出盎然春意、生机和生命喜悦。在邵雍眼中,风月林泉青山美酒如此美妙,可以使他忘却“百病筋骸”而满怀春意,《问人丐酒》曰:“百病筋骸一老身,白头今日愧因循。
虽无紫诏还朝速,却有清山入梦频。风月满天谁是主,林泉遍地岂无人?市沽酒味难醇美,长负襟怀一片春。”大病稍痊、刚能起床,邵雍写到:“病作因循一月前,岂期为苦稍淹延。朝昏饮食是难进,躯体虚羸不可言。
既劝佳宾持酒盏,更将大笔写诗篇。始知心者气之帅,心快沉疴自释然。”(《病起吟》)仅就病痛看病痛,自然是无尽的痛苦;但如果超出病痛的界限,从无限广大的自由之心来看,身躯的病痛就是极为有限,邵雍有了如此超越的视野,很容易做到在诗、书、酒、乐和好友的交游中怡然自得。
衰老之身的诸多疾病并未妨碍恰恰开启了邵雍领悟天地之道的契机。他认为,人生百病有必然的原因,人力与天命之间有不可跨越鸿沟:“百病起于情,情轻病亦轻。可能无系累,却是有依凭。秋月千山静,春华万木荣。若论真事业,人力莫经营。
”(《百病吟》)疾病因后天之“情”而起,这是人生在世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生存宿命。具体到自身,邵雍面对“气滞”和“暑湿”之疾,了悟到:“圣智不能无蹇剥,贤才方善处哀荣。斯言至浅理非浅,少补英豪一二明。
”(《代书寄商洛令陈成伯 》)面对人身难免有疾的实然处境,淡然看待、达观处之,既要少私寡欲、防病于未然,又要因病用药、积极医治。然而,肉身的有限性决定对肉身疾病的治疗也是有限度的治疗,邵雍指出:“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
”(《闲行吟》其一)所以,在邵雍看来,肉身的疾病根本上是一个关涉天人之际的哲学问题,肉身的安顿、疾病的治愈最终要诉诸于对天地之道的领悟。
“人生所贵有精神,既有精神却不淳。弄假象真终是假,将勤补拙总输勤。因饥得饱饱犹病,为病求安安未真。人误圣人人不少,圣人无误世间人。”(《弄笔吟》)对人身的应然存在而言,疾病本身就意味着身体正常功能的残缺、意味着肉身的有限性;勘破天人之际,也就划清了人力和天命之间的界限。在了悟了人力之所为、天命之所定,自然可以妥善处理包括人身疾病的各种问题。
四、死之淡然:借欢乐之生以言说
在“生、老、病、死”的在世生存结构中,前三者可以构成人的生存体验,并有机会被纳入反思的视野而被重新观照,也即意味着可以成为被谈论的话题。“死”却不一样。“生”、“老”、“病”可以被“体—验”,“死”却不可能被“体—验”,否则,“死”就不成为其“死”了;人所能“体—验”到的,最多是“濒死”而不可能是“死”本身。
孔子指出:“未知生,焉知死。”真实言说的前提是具有相应的生存体验。人只有生(生、老、病)的体验,却没有死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死”是一个无从言说的事件。
然而,生与死又是生命现象的一体两面,死亡是所有生命体的必然归宿,它的意义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可回避、不得不被言说。面对“死”的话题,邵雍继承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言说策略,在《击壤集》中借吟咏欢乐之生,表达对死亡的立场和态度。
邵雍首先指出,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重大课题,好生恶死是人们的普遍心态。“恶死而好生,古今之常情。”(《无客回天意》)“恶死好生,去害就利。天下之人,其情无异。”(《好恶吟》)“人生长有两般愁,愁死愁生未易休。
”(《人生长有两般愁》)严格来说,生与死所能界定的,只是作为自然存在的肉身生命,并不能诠释人的生命整体。人作为“文化的动物”,兼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不在于自然生命,而在于与自由意志相关的文化价值。
《击壤集》反思死亡问题,就是在肉身生死范围之外、死亡尽头处发问:“人生固有命,物生固有定。……致死设有因,死外何所求?”(《静坐吟》)立足生生不息的大宇宙宏观视野,进而追寻超越生死的恒常价值。
在邵雍看来,超越生死的恒常价值首先是“义”,并在义利之辨中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两种生命境界。他在《思义吟》将君子与小人做比较,指出君子思义不顾死、小人见利忘义不顾生;在《小人吟》指出小人因为缺乏道德的羞耻感而“重利轻死”。
君子将义视为最高的生命价值,小人将与肉身直接相关的物利作为最高的人生追求。君子和小人都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前者是为理想价值以身殉道,后者是为生理欲望不惜丧身;前者是基于现实人生又超越其上的应然典范,后者是源于自然需求并沉溺其中的世俗人情。
两种价值取向标识了邵雍视域下两种不同的生命活法和生命境界。其次,邵雍指出人情复杂、恩怨深刻,这两者也能超出生死的时间界限:“恩感人心,死犹有喜。怨结人心,死犹未已。”(《恩怨吟》)真诚的友谊亦能经历时间考验而不朽:“金石之交,死且不朽。市井之交,自难长久。”(《把手吟》)这些都表现了邵雍对复杂人性的洞察以及他本人的价值取舍。
对邵雍而言,构成终极价值的绝对之物,并不是义利、恩怨、友情等这些超乎生死的形而下主题,而是超乎生死又超乎这些主题之上的“先天之心”。“先天之心”存在于生死界限之外,构成人之生死乃至宇宙生灭的终极答案。邵雍又将“心”称为“意”,指出其超乎义利、生死的特点:“……利之使人,能忘生死。利不若义,义不若利,意之使人,能动天地。”
正是有了先天之心的存在,后天之身的世界才有了意义,其生死问题的最终解决才有可能。在邵雍看来,离开先天之心的身体缺乏本性的自觉,无异于行尸走肉,其生存于世是一种虚假的生存、其死亡也是稀里糊涂地死去。邵雍将这种状态称为“虚生虚死”:“下有黄泉上有天,人人许住百来年。
还知虚过死万遍,都似不曾生一般。”(《极论》)“卧看苍溟围大块,坐观红日出扶桑。虚生虚死人何限,男子之称不易当。”(《为客吟》)同样,正是在先天之心的烛照下,后天之身的生和死成为一个可以妥善处置的事件。
首先是以淡然的心态顺其天命。《击壤集》多次写到邵雍顺应天命、了悟生死的达观态度:“人盛必有衰,物生必有死。”(《人物吟》)“有命更危亦不死,无命极医亦无效。
唯将以命听于天,此外谁能闲计较。”(《疾革吟》)“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听于天,有何不可。”(《听天吟》)其次是在积极意义上的主动应对。与身心分离、虚生虚死的伪生存不同,邵雍提出在先天之心烛照下后天之身的“真生”和“善死”。
广义上的“真生”,指包括生老病诸种境遇下的应然活法:在先天之心明觉烛照下,康泰之时身体的自在舒展,衰老之中身体的乐天顺化,病痛之际身体的坦然接受……这种“真生”类似于西哲海德格尔的“本真生存”,却带有颇具邵雍特色的欢快和愉悦。这种快乐的“真生”是宇宙生机在人之生命上的油然呈现,是先天之心在后天之身上的透露显发。
“善死”是邵雍明确提出的处置死亡的理想方式:“善死自明非不死,有知谁道胜无知。”(《尧夫非是爱吟诗其一》)死亡时所有生命的必然归宿,是人之与生俱来的大天命,既然无可逃避,就需要积极应对、妥善处置。一方面,“真生”构成“善死”的前提,先天之心的明觉、后天之身的善处是“善死”的必要条件。
邵雍说:“……人鬼无异情,生死有异理。 既未能知生,又焉能知死。既未能事人,又焉能事鬼。”(《观物吟四首其一》)“要识明珠须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
先能了尽世间事,然后方言出世间。”(《极论》)只有明了生的道理,才能明了死的道理;只有妥善处置生的问题,才能妥善处置死的问题。另一方面,邵雍也提到“善死”的一个细节,在《病亟吟》中说:“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
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儒家有“考终命”的理想,是五福之一,可以说这是古人对“善死”的理解。邵雍的“善死”更加全面具体:“死于太平间”而且“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
前者是人之无可选择的“遭命”,后者则是主体道德修炼的“造命”。“遭命”与“造命”辐凑于一身,经由先天之心的觉悟,开启出应然人生的理想境界,并在阴阳大化中与盎然的宇宙生机一体贯通。
如此,死亡本身不再是生命的机械式终结、断崖式终止,也不是孤独个我被生命共同体所抛离;个体的小生命虽死而不灭,以物化的形态依然保持与生命共同体的亲缘共在,“一直因应大宇宙流变不息的感性生命洪流,而处于同步的生成、演变状态之中” 。这正是邵雍“善死”的真意所在。
结 语
邵雍之所以成为邵雍,其生命境界之所以“襟怀放旷,如空中楼阁,四通八达”,并不是因为他能置身于“生、老、病、死”等诸种人生境遇之外,而在于他以高明的易学智慧和独特的先天之学,对人的肉身性存在及其生、老、病、死等生存境遇,实现了一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内在超越。
正是由于邵雍具备清醒的身体意识,关注当下生命的本真感受和体验,兼之先天之心的烛照,其诗意人生免于陷入感性或理性之一隅,而是向大宇宙全方位展开。
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人类的身体是人类灵魂的最佳图画。”沿着《击壤集》中“第一现场”的身体感受和体验,从身体维度切入邵雍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重新审视其身与心、性与情、物与我、先天与后天及其天人境界,使邵雍哲学研究获得了生存论基础,应当可以展现出邵雍思想更加亲切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