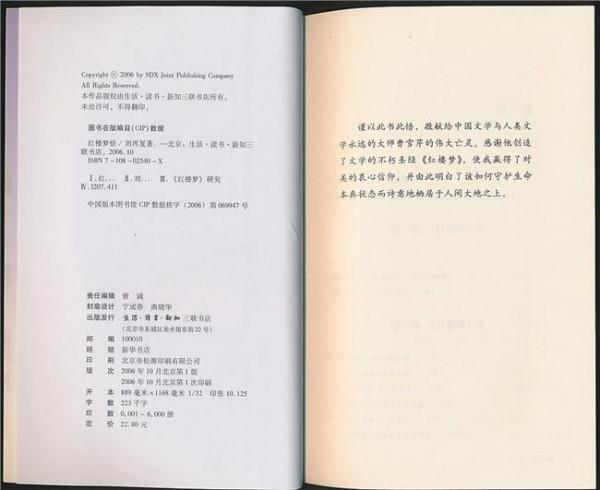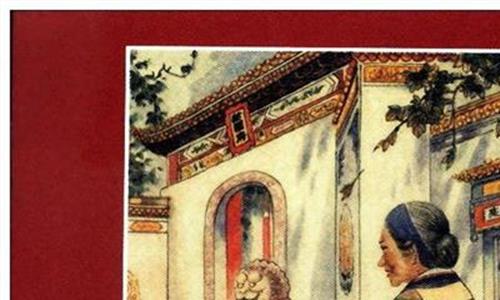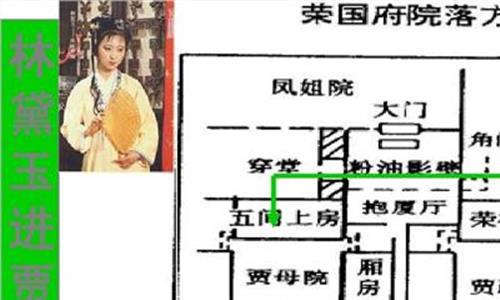刘再复红楼梦 刘再复:《红楼梦》阅读悟语
《红楼梦》整体(一百二十回)最后结束于一个哲学地点,叫做“急流津觉迷渡口”。这一渡口名称不可忽略,尤其是“觉”与“迷”二字。佛教乃是无神论,它以觉代替神,所以慧能认定,悟(觉)则佛,迷则众。小说结局,其人物或觉或迷,或佛或众,就在“觉迷渡口”上分野。
贾宝玉始于痴,止于觉,终于“走求名利无双地,打出樊笼第一关”(第一百一十九回)大彻大悟而解脱了。而另一个本来也有颖悟之性的贾雨村却觉不过来。第一次是甄士隐来开导他,但“雨村心中恍恍惚惚,就在这急流津觉迷渡门草庵中睡着了”。
第二次是空空道人将抄录的《石头记》给他看,“复又使劲拉他”,他才慢慢的开眼坐起,接过来草草一看,作了交代,“说毕,仍旧睡下了”(第一百二十回)。一个醒悟了,一个睡着了。《红楼梦》这一终结,是禅的启示性终结,极为成功的总句号。小说的续书,有妙笔、有败笔,而最后这一笔则可称为神来之笔。
重物不重人的世界
贾宝玉到人间走一遭,体验着人,体验着世界。回归青埂峰前,对人最根本的失望,也可说是绝望,就是人太重物质而不重自身。他对宝钗、袭人说:“你们这些人原来重玉不重人哪!”(第一百一十七回)这是他告别人间之前最深的感慨,也是最深的忧伤。
人呵人,原来都是没出息的人,原来都是势利的人,原来都是被物质抓住灵魂的人,原来都是被色欲迷了心窍的人,原来都是把玉的价值放在心的价值之上的人。轻重颠倒,本末颠倒,心物颠倒,形神颠倒,可是,人人都自以为是,以为宝玉又说疯癫话了。
心外无玉
第一百一十七回(“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成家”)记载贾宝玉出家之前癞头和尚来索玉,宝玉想还玉,宝钗、袭人拼命拦阻。袭人说:“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拿去了,你又要病着了。”宝玉道:“如今不再病了,我已经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
玉是至贵之物,但毕竟是物。《红楼梦》的大哲学问题之一是心与物的关系。是心为本体,还是物为本体,是心为第一性,还是物为第一性,是心至贵,还是玉至贵?关于这个问题,宝玉最后作了回答:“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 一点也不含糊。
佳人们以为他在说疯话,其实,这是最清醒的人所表达的最清明的意识:天地万有,具有最高价值的是人不是物,是身内之心不是身外之玉。贾宝玉经历了一回人生,体验了悲欢离合,一悟再悟,最后终于赢得心觉:有了心了。到地球上来一回,有了心,算是明白人,便不虚此行。
心的深邃
曹雪芹与王阳明都是大“心学”家,堪称中国精神大地上两座心学高峰。但读王阳明的心学,只知心的重要,而读《红楼梦》,才知道心的深邃。曹雪芹笔下的心,是深海深渊,是无限的时空。对于王阳明,可以用学去把握,对于曹雪芹,却只能以悟去把握,非有无尽之情难以进入其无尽之海。
王阳明的心学展示在概念中,曹雪芹的心学隐藏在人物的意象中。心为世界本体,除了心之外,其他物质皆为幻象,这是两位大心学家的共识。王阳明之心可以分析,曹雪芹之心无法分析,它只能意会,只能神通。对王阳明的哲学可以论证,对曹雪芹的哲学,则只能悟证。
秀美史诗
《圣经,旧约》中的耶和华,非常强悍,动不动就发怒,以致要毁灭城市。作为文学作品,《旧约》体现的是壮美风格,《新约》中的基督倒是具有女性色彩,但没有改变女人是用男人肋骨所制成的神话,因此并没有改变性别歧视的宗教源头。
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家在《旧约》中找到男权统治的源头,中国则在《论语》中找到源头,于是才有“五四”批判孔夫子而为中国妇女请命的运动。曹雪芹的《红楼梦》承继《山海经》的文化基因,把女娲(母性)视为创世的第一动力,把女子提到形而上的神本地位。
《红楼梦》开篇讲正气、邪气、秀气三气造人。贾宝玉、林黛玉及其他青春女子全是灵秀之气所生,这一哲学基点,便决定了《红楼梦》的总体风格是秀美,不是壮美。作为史诗,便是柔性史诗,不是《伊利亚特》式的刚性史诗。中国文化从老子开始确立的尚柔传统,到了《红楼梦》便发展到极致。
无算计思维
以撒·柏林在与拉明·亚罕拜格鲁(Ramin Jahanbegloo)的对话录中,曾引用哈曼(Hamann)的话说:“上帝不是数学家,而是艺术家。”(《以撒·柏林对话录》,台北正中书局,杨孝明译,1994年,第8页)我们可以引申说,不仅上帝是艺术家,基督和释迦牟尼也是艺术家,他们因为没有算计性的思维,所以才有大爱和大慈悲。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因为“机关算尽”,所以离上帝、基督、释迦特别远。我把宝玉视为未成道的准基督与准释迦,因为他也是艺术家,完全没有数学机能。
他爱姐妹,也爱探春,但是当探春主持家政,精细地算计到“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第五十六回),甚至想把蘅芜苑和怡红院的花草也出售赚钱时,他就受不了,并对探春很有微词。他和探春的冲突,是艺术家与数学家的冲突,也是《卡拉玛佐夫兄弟》中那种基督思维与大法官思维的冲突。
人鬼之道无别
《红楼梦》让地狱的判官说出一条骇人听闻的真理:阴阳并无二理,人鬼之道并无二致。这是第十六回中秦钟魂魄请求还阳片刻,鬼判们说出的大实话。都判官听到秦钟说到“宝玉”二字唬慌起来,众鬼便说:“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电雹,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
依我们愚见,他是阳,我们是阴,怕他们也无益我们。”都判道:“放屁!俗语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事’,自古人鬼之道都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人世界与鬼世界没有两样,阳间的官僚与阴间的都判差不多,自古皆然,从来如此。
曹雪芹的哲学是阴阳一体,即史湘云对翠缕讲的“阴阳两个字是一个字”(第三十一回)与都判官所说的并无差别,只是都判官更落实,直接破道“人鬼之道都是一般”。是一般黑还是一般白,是一般无诚实可言还是一般无廉耻可言,他“老人家”没讲清楚。但说人之道与鬼之道是一回事,却是真话。鬼话有时比人话还坦率。我们固然不能因人废言,恐怕也不可因鬼废言。
垂头自审
“宝玉闷闷地垂头自审”(第二十二回),这句话最能体现宝玉的佛性佛心。佛有喜相,也有忧相,但没有我之执相,人之妄相,众生之俗相,寿者之老相,凡遇矛盾冲突,不把责任推向对方总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自审正是佛性的第一特征。
读遍《红楼梦》,见到数百人物,唯一能够“垂头自审”的人只有贾宝玉一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我膨胀,只有一个口衔玉石而降生的被视为呆子的人能够反观自己,能够以他者为参照系而看到自己是“泥猪癞狗”、“粪窟泥沟”(第七回,宝王见到秦钟之后的自惭之语)。
还有一个原也自以为是、但终于正视自己的致命错误“耻情而觉’’的柳湘莲,可惜在尤三姐洒尽碧血之前他也自视太高。至于贾赦、贾政、贾敬这些老爷和王夫人、邢夫人这些贵妇及贾琏、贾蓉这些少爷们,除了自美、自炫、自负之外,一点也沾不上“自审”、“自耻”的边。
曹雪芹在“垂头自审”前加上“闷闷”二字,极为妥帖。老子《道德经》上说:“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俗人都聪明绝顶,唯独宝玉是个傻子。
破性别“执”
贾宝玉是单性人,还是双性人?或是中性人?读者爱问他是谁。西方的《红楼梦》研究者也喜欢提问他是何“性”人。从精神归属上说,他既不是大仁之人,也不是大恶之人,而是正邪组合的中道之人,即第二回贾雨村哲学分类中的“第三种人性”:超越大红大黑的灰色地带人。
从自然人性层面看,他爱青春少女,也爱青春少男,倾心于两栖,既是快乐王子,又是“绛洞花主”。这奥秘,是他天生一身佛性,天生没有我执,不执著于我是谁,不执著于世俗角色,不执著我为何物何人,甚至不执著我是男性或女性。从各个层面打破执,打破隔,才有大爱与大慈悲。宝玉正是彻底打破我执法执的真情真性人。
重在心灵
孔子之思,侧重于人际;孟子之思,侧重于人格;屈原之思,侧重于社稷;杜甫之思,侧重于民生;陶渊明之思,侧重于自然;曹雪芹之思,则侧重于个体生命的心灵。《红楼梦》主角贾宝玉从不为人师表,唯有一次开导芳官,说敬神敬人应贵在“心诚意洁”,而他自己最高的觉醒是心觉,出家前夕,他说:“我已经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宝玉说的“心”,不是胸膛中那颗肉做的心脏,而是真心。
即不是本能之心,而是本真之心。真心直观万物又主宰自身的生命,包括统率本能。
梁漱溟先生在《孔家思想史》中说一切柔情都出于真心而不是出于本能。因为本能只是手段,真心才是真正的主宰。有了这一主宰,“人”才不为“物”役,也才不为“玉”等财色所役。佛学中讲的心也是真心,包括六根在内的全部生命感知系统。所谓观,也不只是肉眼的看,而是全生命系统的通观。中国文化系统中“心”一词的至深至广涵义,就蕴含在《红楼梦》中。
不争之慧
《红楼梦》全书只有一次论辩,这是第一百一十八回宝玉与宝钗关于“人品根柢”,“赤子之心”的论辩。宝玉与黛玉多次吵嘴,但不是论辩。宝钗是贾府中的女孔子,她远离禅,所以需要争论。禅的明心见性,没有思辨过程,也没有讨论过程,它不相信真理愈辩愈明,只道破真理即发现真理。
庄子和惠施有关于鱼之乐的论辩,那是直观方式与逻辑方式的论辩,慧能则从未有过论辩。唯一的一次是在他人进行风动与幡动的论辩中击点要津,道破非幡非风而是“心动”,他知道论辩是种陷阱,热衷论辩只能让自己活在他人预设的前提与框架中,甚至让自己在扭打中发疯。
大智慧者不进入“请君入瓮”式的圈套。《红楼梦》的哲学方式是禅的方式,贾宝玉从不承接他者的话题与前提,不予论争,无论是对甄宝玉的酸论和对于父亲的批评。他的不争之德使他得大自在——未得大自在之前,也得了许多小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