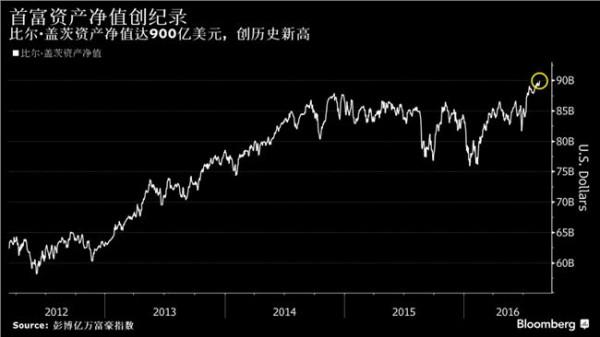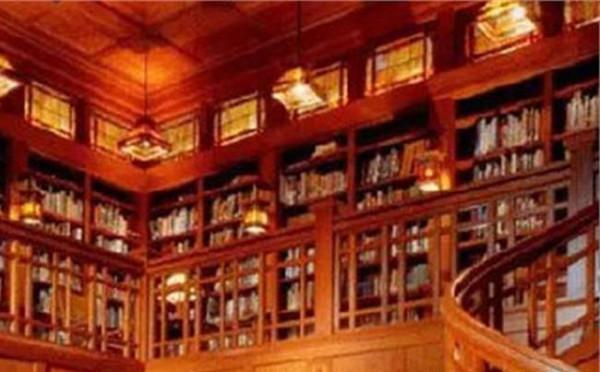巫昂的杂文 比尔 盖茨的礼物(短篇小说) ∣《文学青年》巫昂专号至尊神位
我叫以千计,我曾经干过很多行业,最近这个阶段,市道不景气,好工作难寻,所以我在家写小说,休息的时候,帮我妈摘摘菜叶子。每当我以谦恭儒雅的语气,向陌生人这么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被对方猛打一个耳光,厉声道:好好的人不做,起个日本名字干吗?
我每每错愕,不知所措地摸着自己滚烫的脸颊,对方显然没有听完我的详细资料,这时代人心真是浮躁,听人说话听一半儿,结婚结一半儿,死都死一半儿,不甘心过世的人,常常会从病床上爬起来接着摘菜叶子。
揉一揉几近落枕的下颚,我很有耐心地继续对他说:一年前我还不叫以千计,但写小说的人要有笔名的,就好像自行车运动员先要置办头盔,再弄肌肉。我就是嫌弃本来那个名字不好听,才写小说的,这样我才可以心安理得地起个笔名。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有过156个笔名,笔名多得下了班回家一看,家里挤满了人,团团围住许广平和周海婴,人们络绎不绝地来认自己的真身。普普通通的笔名我又用不惯,所以,我叫以千计。
那你原来叫什么?以百计?
这人真是聪明,他接下来还能猜得到我未来的笔名,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省心。当我在作协文联大楼下,直接站在雪堆里以示诚意,为谋得一套来年的秋裤瑟瑟发抖,我满怀悲怆,我的命运就是如此:以千计!
刚开始写小说那会儿,其实也就是去年春节过后,春节过完,吃吃喝喝尘埃落定,我才正式下定决心的,我要开始作为一位叫做以千计的小说家而存在的新生活了。
用上一份工作存下的钱,凑上我妈的买药钱,买了整洁的书桌,带靠背的椅子,一叠稿纸,和一打笔。
开头我确实以百计,一个礼拜只能写一百字,余下的时间,我妈也没有那么多菜让我摘。那我就遵循旅美作家哈金的教导,写不出来也要坐在桌子跟前,坐够八个小时再下班。写小说要有写小说的样子,就跟和尚上班就得坐在菩萨跟前一样。外头工作你嫌不好,这家这工作你可不能再嫌弃了。
我抚摸桌子的棱角,收拾抽屉,把笔帽跟笔杆子来回套。
就算我这般清心寡欲,心诚意洁。外边那浮躁的社会也没能放过我,作协找我谈话,文联请我汇报思想,我一一回避,把电话线拔了,连通往我妈那套单元房的小门,都上了锁,轻易不过去看。
我妈不干了!眼看我两礼拜没过去摘菜叶子,心想孩子还像不像话了,没工作不说,连摘菜叶子都想赖过去。我妈过来找我做思想工作。
孩子,须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成天石雕一般一动不动,让我如何心安?
我已三十五岁,成年男性,生活可以自理,只是不愿意以摘菜叶子度过余生,等您百年之后,我自然过去探望。
我妈照例甩了我一个耳光,我妈与他人不同,是左撇子,所以我的右脸有幸得到一下耳光。一向备受轻视的右脸全靠我妈关照。
随后,她在我的小说当中,愤然离世,把肥胖的身躯遗传给了我。
好在母子情深乃是万古伦常,她有意留下清汤一碗,我悲怆喝完,胃肠感到了春节以后的第一次滋润,牛骨清汤!正宗牛街牛骨,从一头新鲜的牛身上崴下来的。我妈坐了轻轨在四惠东换地铁,从国贸口出去,又倒了两路公交,方才赶在早上人潮汹涌之前抢到那根牛骨。
一头牛身上,只有两根那么熬得出汤的骨,我妈品位不俗。
可惜她老人家只剩下清汤一碗,两袖清风去了,这就是我的命运哪!自她走后,上天感念我的诚意和决心,让我的写作速度自动升级,一个礼拜能写一千字。
所以,笔名更新到2.0,成了以千计。
傍晚时分,我友墨子来访。
他脑门很高,穿着一件过了时的深蓝外套,头顶同色带檐软帽,一脸衰气,活像文革时候北京老百姓的造型。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搞不清楚阿拉斯加和拉斯维加斯到底相隔多远,墨子对我国的近现代史那是相当地糊涂。他在他那个暗无天日、没电灯没电话的时代,辛辛苦苦攒点钱,想出趟远门,实现一生的梦想,去趟未来。
墨子本人是很节俭的,买了火车票准备到2009年,为什么到2009年来,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这就是人说的命运吧,蒙了一个看起来还算不错的数儿。不料历史的列车停在1971年,人潮汹涌哪,红卫兵要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墨子眼见一群群深蓝外套,同色软帽,心里头一激动,赶紧脱下自家麻布长袍,献给那帮小兄弟。小兄弟接了过去,没有作揖回礼,还拿枪杆子捅了墨子一下,他的肚皮上顿时出现了一个坑,好在不出血,人太古老了,流不出血了。
列车嘟嘟嘟开走后,墨子光溜溜站在站台上,瘦得跟驴子似的,生殖器上裹着一片干树叶,拿麻绳绑着,相当滑稽,一点都说不上高古俊朗。来来往往的红小兵正当青春,在他们自己的年代里蹦跶,视他若无物,有人踩了他一脚,也有人把他的胳膊撞到乌青。
哎哎哎!我是云梯的发明者啊!他叫道。没人理睬他。
我……是……云梯……的……发--明--者。
第三天半夜,因为肚子饿,他呻吟了一下,继续喊道,想博口水喝。却被一位着急赶夜火车的乘客,一脚把他碰飞,他整个儿顺着站台,滑到存货的另一角,也该他着,那里躺着个死去的红小兵,看模样,他在那里呆了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死尸不可怕的,墨子打过仗,他明白怎么跟去世的人相处。
墨子机智地剥下了那位兄弟的深蓝外套,同色软帽,也登上了同一车次的夜火车,人们对他态度顿时改变,他混在里边,在一片深蓝中深陷。再也不敢提云梯的事,云梯云梯,那都是可以爬天安门城楼的危险物件,不能提不能提!
墨子是哲学家,哲学家这工作,管吃一堑长一智的。
我友墨子不是日本人,更不是女人,女人就糟糕了,得留刘海,还得穿胸罩,成何体统?他是个哲学家,读过书的人都认识他。为什么我能够交往到这么有头有脸而且过世多时的朋友呢?这就是写小说的好处,在小说里边要跟谁交朋友都可以。不信下次我写给你看看,本拉登和戴安娜跟笔者,也都算是至交。说这些名字太俗,有攀高枝儿之嫌疑,我作为一位一生立志写小说的奇人志士,自然不耻。
事情有时候也有意外,我把我妈交给我去楼下买菜的十块钱弄丢了,我硬说是掉在菜摊子缝里找不回来,卖菜阿姨对我相当不满,没见过我用这种手段赖给人的。从此对我们全家就有些淡淡的,连我妻子都遭殃,卖给别人西红柿一斤五毛,她的偏生五毛五,她也委屈得不行。
提起我的妻子,那才叫悲怆,早在我妈消逝之前,我早已把她写没了。
这女人家腰身又不细活,成天在家聒噪,一个月倒有三十五天经前综合症,一会儿让我出去买酸梅汤,一会儿让我给她二舅找个名医看耳鸣。弄得我很烦。性生活方面我们早已貌合神离,我明明在上面忙碌,她下面却喊疼。我只好停下,爬去查看下面,却见下面气定神闲,里边好像还有两只小鸭子在戏水。
我很生气,转身睡自己的觉。她越发不满,刚想张口再度提出离婚,老调重弹老调重弹,离婚会离死人吗?大街上有一半儿成年人离过婚,我才不追求那种时尚呢。
我一时恶从胆边生,起身披衣,走到桌前,开了台灯。就着灯影,拿起笔,划拉两下,把她写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