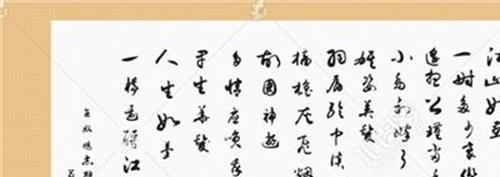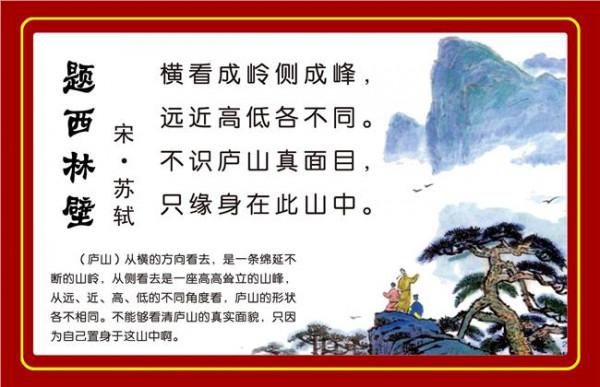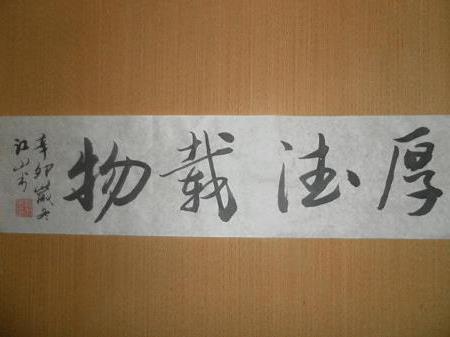念奴娇.赤壁怀古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豪放词吗?
说到宋词,历来有婉约派和豪放派之别。有宋三百余年,婉约派是当然的主流,从北宋的欧、晏、柳、秦、周到南宋的姜、蒋者流,无不因婉约词而名留词史。至于豪放派,尽管作家作品不多,但成就斐然,不容小觑。苏辛并称,震烁千古,他们的成功历历在目,不是我要写的重点。我这回想谈谈历来被目为豪放词代表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关于它的性质也许并不像我们以往想得那么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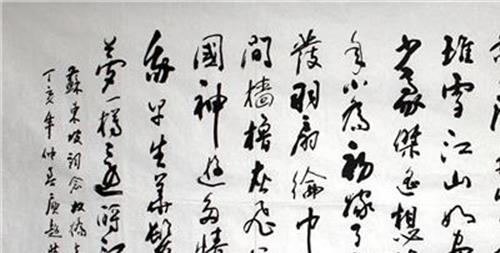
苏轼往往被看作改变宋词气质的关键性巨匠。苏轼以前,从唐到宋,词都是妩媚绮靡的风格。剪红刻翠,儿女情长,离愁别绪,相恨相思,这些温柔缠绵的内容被宋朝的公卿士大夫反复把玩,犹如摩挲精美温润的玉器。这与宋朝优待士大夫的政策有关,也与宋词民间文学蓬勃发展有关。

当词人们在温柔乡里浅斟低唱的时候,范文正公在西北边陲唱出了《渔家傲》,以悲凉雄壮之笔写军旅生涯;欧阳修也不经意写出“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盅”这样豪迈可喜的句子;贺铸除了博得了“贺梅子”的美誉外,也有“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的男子汉气概。不过这些都只能视为豪放派词的铺垫,真正的主角还要算苏轼。

是苏轼彻底改变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词在苏轼的手里变现力大幅度提升,举凡谈文论史、怀古伤今、志趣爱恋这些诗的素材都可以用词写出来。音乐性原本是词必备的属性,但苏轼不愿受格律的限制,突破了很多形式上的桎梏,词由此成为了句式长短不齐的新诗体。

那么问题来了,苏轼一生词作颇丰,究竟哪些词是豪放词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脱口而出:《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宋词的历史上,以及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这首词都是大大有名的。相信只要读过中学的人都会对它有印象。这首杰出的词作几乎是苏轼最高的成就了,千百年来喜欢它的人不可胜计。我有一点拙见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首词固然绝佳,但归类为豪放词似乎不妥。
首先要弄明白“豪放词”这个概念的含义。豪放作为文学风格,见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反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
这种文学性的描述恍惚难辨,大体说明了豪放的风格有元气充沛、精神自由的特点。杨廷芝解释豪放为“豪迈放纵”,即“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诗品浅解》)。可见豪放的作品当气度超拔,不受羁束。
然后再来细看《念奴娇·赤壁怀古》,上阕写黄州赤壁的壮丽景色:大江奔涌,山壁峻拔,惊涛如雪,风光如画。苏轼目睹此景,追溯历史,想到曾于此地留痕的杰出古人,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江山壮丽,人物风流,苏轼以爽朗激昂的笔墨挥洒开来,读来令人豪情顿生。
下阕里,苏轼于众多三国英雄人物中择出周瑜来,着力写这位青年将领的雄姿英发、爱情美满和谈笑间挫败敌人的儒将气概。读者读到此处往往精神勃发,眉飞色舞,飘飘然有凌云之志。苏轼本人又怎么样呢?可能有人会认为苏轼也与读者有同感吧?
但我借用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话来说:
“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江山这么壮丽,人物如此了得,跟我苏轼又有何干呢?假如周瑜神游故国,看到多情的我早生华发,他一定会笑话我吧?哎,算了,算了,举一杯酒酹于江心的明月,原谅我这不堪的命运吧。想我苏轼,少年拼搏,青年中第,原以为从此能干一番大事,可宦海浮沉十几年,到头来一事无成,毁谤满身,被贬荒地,九死一生。跟青年才俊周瑜相比,我是多么无奈、多么失败啊!
乌台诗案,千古奇冤,是典型的黑暗的文字狱。一个放言无忌却又心思单纯的大才子被变法小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的苏轼料想自己必死无疑,于是在黑暗腐臭的牢房写一份遗书给弟弟苏辙: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这首令铁石人落泪的诗差一点成为苏轼的绝笔。万幸之余,被贬黄州,他的生活境遇怎么样呢?请看下面这个片段: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这哪里有我们熟知的苏东坡式的潇洒风流?他仰天悲嚎,他无能为力,惨淡的命运在尽情地折磨着这个苦命的读书人。不要被《定风波》的旷达自得所“迷惑”,苏轼的黄州生活远没有那么诗意。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过上了神仙的日子”,我表示不敢苟同。
不过有一点应该承认:苏轼心宽,坚强乐观,能够在苦难的缝隙里挖掘快乐。他可以忍受耕种的辛苦,可以跟渔夫农妇打成一片,可以笑傲风月,可以在佛教的怀抱里寻求片刻解脱。苏轼以充沛的生命能量支撑起北宋文学的最高峰,并以其乐观豁达的精神品质赢得了后人的尊重与喜爱。苏轼集士气、仙气、世俗气于一身,高雅而通脱,庄重而活泼,这种人格范型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可视为儒释道三种哲学水乳交融后的伟大成果。
说了一大圈,回到正题来,《念奴娇·赤壁怀古》仅有豪迈的表象(我不忍心说是“假象”),但骨子里却是浓浓的挫败感、自卑感,以及自我宽慰的无力感。它的情感由开阔的长江起兴,转而赞佩古人,归结为对不堪命运的自我抚慰,从波澜壮阔到平缓黯然,结尾的“还酹江月”陡然间为全词蒙上了辛酸灰暗的色彩。
自伤自怜的苏轼悄立岸边,暗自嗟叹,他苦笑着摇摇头,跟自己握手言和了。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里认为,苏轼在苦难的洗礼后终于成熟了,找到了安顿灵魂的方式。的确如此,苏轼收敛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情,熄灭了“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壮志,只愿“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总结一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其实主要写的是作者心中的伤感,而非壮志豪情。因为没有壮志豪情,也就没有了豪放词该有的“豪纵自是”。按照“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的标准看,苏轼此时万念都息,与世无争,以江湖隐士自居,放达过人,豪迈不足。《念奴娇·赤壁怀古》貌似豪放,实则黯然销魂。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附上几句题外话。豪放词的诞生一定需要合适的土壤。盛唐的李白可以豪放,他坚信自己赶上了伟大的盛世,“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岳飞可以豪放,他坚信自己手握重兵,令行禁止,所向披靡,一定可以迎二圣还朝,“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只有看见希望的人才有豪放的可能,黄州时期的苏轼显然不属于这类人。就连豪放词的另一位巨匠辛稼轩,也并非每首词都是豪放词,其中的郁闷和伤痛都是一览无余的。他排遍栏杆,在夕阳的余晖里偷弹恨泪,渴望有红巾翠袖为自己拭泪而不可得。他的英雄气被冰冷的现实消磨殆尽,最后的绝唱“可怜白发生”就是梦醒时分的悲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