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说成都李劼人 李劼人笔下的成都
前几天看淡豹的日记谈到李劼人先生和他的《死水微澜》。其实《死水微澜》后面还有《暴风雨前》和《大波》,合称为“三部曲”。只不过后两曲没有前面的《死水微澜》那样有名。我现在手中这套书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据出版说明上说出这套书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把李劼人写的《天魔舞》寄回四川了。这本书后来也出版了,我没有读过。手头有他来往书信的一个汇编。记得我到重庆经典书店的时候,有人问我是不是受汪曾祺先生影响较大,他说我看书的腰封上印着那样一句话。
我想了一会,这就象忽然问一个人身上肌肉是吃什么长起来的一样。你没办法具体到肱二头肌是吃鸡肉长起来的,三角肌是吃牛肉长起来的。读书大部分都是东读一点,西读一点。然后构成你自己的叙述方式。
我个人觉得受四川两个作家影响比较大,一个是李劼人、一个是沙汀。以后要到成都去一定要到菱窠去拜一拜。 汪先生文章中比起小说来我更喜欢他的散文。比如说《泡茶馆》、《跑警报》、《昆明的雨》、《观音寺》,这几篇散文在新出的书中都有重复的收入。
汪先生的散文中我觉得《昆明的雨》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比如他写道“——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不动在屋檐下站着”。真是神得之笔!
出版过的汪先生的书大部分版本我都有,比如有的版本中有汪先生写的一句骂人的话,后来再出就删掉了。后来我看这篇时就觉得好象少了什么东西。这回淡豹拿来跟李劼人做对比那篇小说,写谢普天与小孃孃之间的不伦之恋。
其实当时我看了这篇小说也是心里格登一下,我心说这老先生这篇不在状态呀!心里觉得这篇写得很雾数,这种雾数不是不伦之恋本身产生的。而是作者的一些叙述方式出了问题。《小孃孃 》有可能是老先生犯了糊涂劲写出来的,也可能却不过人情硬憋出来的,如果让他自己选,他不至于选到小说集中去。
过去我家书橱里除了我爸爸单位发的马、恩、毛著作之外,闲书也没有几本。夏天放暑假的的时候。我在书橱里翻出《死水微澜》和《沙汀短篇小说选》,消磨了一整个暑假。
上午做完家庭作业之后,扛一床篾席子跑到走廓里铺下来,看累了就睡一觉。醒了再看。看了许多成都好吃的,口水淌了一席子。我看中国介绍外国文学翻译的历史时,没听到什么人提起他。
其实《萨朗波》和莫泊桑都是他绍介到中国来的。他是一个被严重低估了的小说家和翻译家,李劼人的好处是语言锤练得好,许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做小说有一种“牛油”气和“翻译腔”。李劼人先生在这一方面淘洗得比较干净,他揉合了章回小说和成都的口语,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川派的小说的的做法。
《死水微澜》这本书的背景大致在一八九四到一九零一之间,小说一路写到“保路”运动和四川独立。“保路”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风潮,起因是朝廷与民争利。
把本来从民间募集股本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这真是一个昏招!把社会上各个级层都得罪完了。本来同盟会当时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受教育的人群当中,会众是一班读书人和受过西方思潮影响的学生。
大清取消了科举之后,这批人要找出路。通过读书取仕的路被堵上了。后来有一些革命党人私下说,要是还开科取士,我们也不至于出来搞同盟会。但底下一般老百姓对他们这种革命并不同情,认为他们到处暗杀,甩炸弹是乱党,无父无君之辈。
跟他们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所以有鲁迅写的华老栓那种底层老百姓的形象。“保路”运动一下子把这些力量捏合到一块来了,虽然诉求不一样。但不妨碍他们伙在一起搞垮大清。所以当时四川要求独立的同志军队伍里有哥老会的,也有土匪(棒老二),扛着三眼铳和梭镖、大板刀。
学生军则一人掌中托着一个炸弹在游行,神情肃杀。围观的群众说就这么一个小小炸弹一丢能把全城的人炸得死光光。他们闹了几个月后,四川终于独立了!
有历史学家说没有四川的“保路”运路,武昌起义能不能成事还两说。 李先生擅长写四川女性。我觉得后面的两部小说没有前面那么好,主要是缺少一个好的女主角。就象船没有风一样,整个情节就懈下来。你比如说他在《死水微澜》中塑造蔡大嫂这个人物,她本是一个乡下的幺姑娘,对成都生活充满了向往。
胆子大,人又泼辣刁蛮。张大千说世界上美女有三等;其中一等是泼、辣、刁。泼、辣、刁这三个字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至。她这样一个人岂是一个小小兴顺号能牢笼得住的。
她只不过在等待一个机会。罗歪嘴带着刘三金回到天回镇开赌局,好戏才登场。剥剥杂杂象野火似的烧起来,先是一线如蛇般蜿蜒曲折。等到了烧教堂,官兵吹着过山号来抓人的时候,打了蔡兴顺,她象一匹老虎似的扑上去咬打傻子蔡兴顺的兵丁。
蔡大嫂在整个人物就立起来了,比如后来她要改嫁顾天成,她的父母说:“那怎么使得?我们的女婿还在呀!”。“蔡大嫂猛的站起来,把手向他们一拦,脸上露出一种又惊,又疑,又欣喜焦急的样子,尖着声音叫着:“怎么使不得?只要把话讲好了,可以商量的——“。
事后她解释自己为什么答应这桩婚事,她说:“你两位老人家真老糊涂了!难道你们愿意你们的女儿受穷受困,拖衣落泊吗?难道你们愿意你们外孙儿一辈子当放牛娃儿,当长年吗?放着一个大粮户,又是吃洋教的,有钱有势的人人,为啥不嫁?”这段话说得太好了,我都想用毛笔把它抄出来裱成镜片发卖。
她的父母还在嘀咕说:“就不怕旁的人背后议论吗?”蔡大嫂回答说:“哈哈!
只要我顾三奶奶有钱,一肥遮百丑——怕那个?”。蔡大嫂能有这种见识,一方面是自身的慧根,另一方面也确实有大时代的影响。怪不得蔡大嫂的老爹感叹:“世道不同了!”。 李劼人先生小说中的人物是贴到成都当地的风土民情来写的。
虽然说外面又是义和团、又是八国联军,又是同盟会走马灯一样。但成都作为偏处一隅的内地城市,一般市民与士绅生活还是很安逸的。就象海面还卷起了八级狂风,但海底的扰动还是极小的。
这些扰动非常小,象一丝微风努力在吹一页书,终于翻过来了。他写开明绅士家里用的保险灯、自鸣钟、洋胰子、香水、到一般普通老百姓用的洋针、洋线,以及外来信仰跟本地信仰的冲突。顾天成被洋药起死回生之后,他对洋人的东西一则以喜一则以疑。
顾天成的信教,完全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信了教他就可以复仇,可以烫罗歪嘴他们的“毛子”,可以要回被宗亲霸去的田庄,甚至连田庄里被撵出去的花狗也能找回来。
这在过去他作为一个土粮户,吃了官府或者帮会的亏那只有自认倒霉。现在顾天成多了一种选择,有什么理由不去选择信洋教呢?顾天成和蔡大嫂这两个人是得风气之先的人,结果这两个人走到一块来了。 李先先写作时有个毛病。
写到吃的时候往往不知节制。所以看他的书要淌好多口水。他说:“中国人对于吃,几乎看得同性命一样重。这不但洋人不能理解,就是我们自己,亦何尝了解得许多!“。他在小说中花好几页纸写这道菜怎么做的——比如婆婆豆腐,他这样写道:“于是老板娘便发明了作法,将就油篓内的菜油在锅里大大煎熟一勺,而后一大把辣椒末放在滚油里,接着便是猪肉片、豆腐块,自然还有常备的葱啦,葱苗啦,随手放了一些,一烩,一炒,加盐加水,稍稍一煮,于是辣子红油盖了菜面,几大土碗盛到桌上,临吃时再放一把花椒末。
劳动家一吃到口里,那真窜呀!”,他的这种写法简直可以拿来照方抓药做这道菜。 他说成都人特质是爱“找舒服”,“懒散得近乎随时随地找舒服”。
小说中有许多场景是在茶馆中发生的,他在书中这样写道:“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人家祠堂内。
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议好事歹事都在茶铺里”,议得不好就要打架,打架也在茶铺里面。茶铺老板也并不害怕别人的打架,等打完架以后,他就好出来点数打烂多少桌椅板登,打烂多少茶壶茶碗。
然后偷偷把灶间藏的破碗、破壶也算在内,打架对于他并没有什么损失,反而还能小赚一笔。狡黠得令人心生欢喜。由这种懒散生出许多闲情,比如说成都人爱看热闹。就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一个成都的朋友,她说成都人是蛮爱趁热闹的。
成都地铁通的时候,几乎是倾城出动,就这头坐到那头。然后再坐回来,好过瘾啊!李劼人以一个具体的城市做背景展开所有的人物,当时流行的小说做法连城市的名称都不说,只有a城b城来代表。人物或叫C君,或叫W女士。
这样的城市和人物叫法我老是读着不舒服,另外有一种做法就是城市靠海的就叫滨海市,临河的就叫沿河县,村子有棵槐树的就叫槐树庄。这种叫法我也觉得不亲。李先生是连成都婚丧嫁娶的仪注,每一年的物价变化,穿戴,世态语汇都做记录。
比如“撒葱花”“煮屎”“苏气”——象他这种小说做法,外国有个帕慕克与他有点相似,这个人是所有故事的背景围绕着伊斯坦布尔发生。作为小说背景的城市要有适当的规模。城市规模太小,许多故事成立不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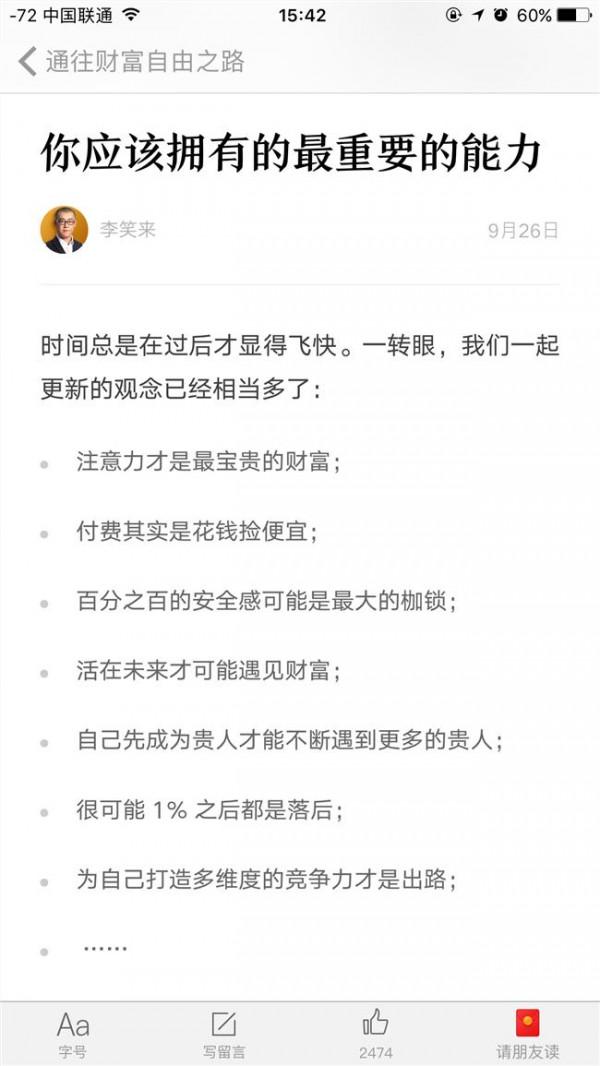



![>李约瑟全名 [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评选]李约瑟:让中国古代科技扬名世界的人](https://pic.bilezu.com/upload/d/73/d73e23c9f21c443aa95055b363a945fa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