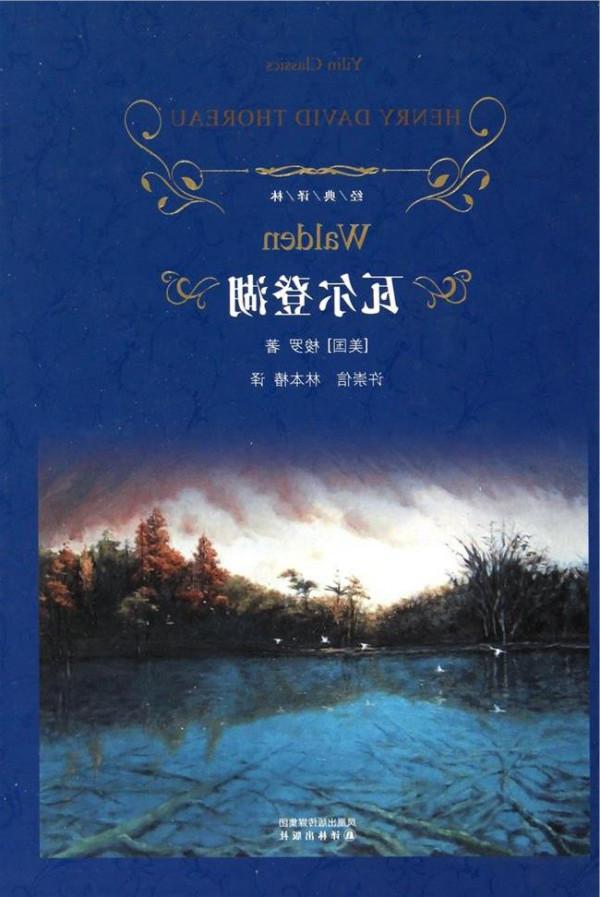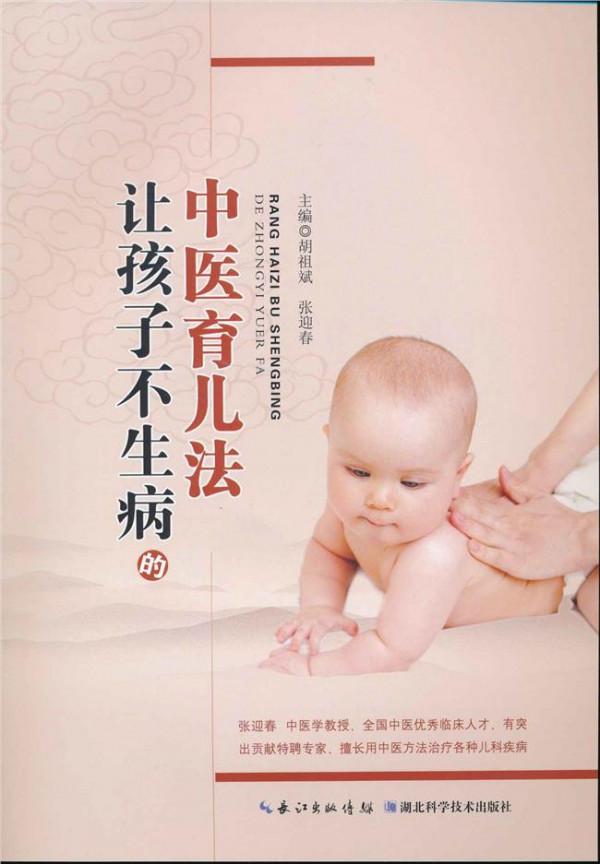【梭罗瓦尔登湖名句】瓦尔登湖 梭罗的湖
想为一本寂寞的书打破一点寂寞,此愿巳久,这本书就是梭罗的《瓦尔登湖》。
这本书在一八五四年出世时是寂寞的,它不仅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甚至连一些本来应该亲近它的人也不理解,对之冷落甚或讥评。它永远不会引起轰动和喧嚣,在它成为一部世界名著之后它也仍然是寂寞的,它的读者虽然比较固定,但始终不会很多,而这些读者大概也是心底深处寂寞的人,而就连这些寂寞的人大概也只有在寂寞的时候读它才悟出深味,就象译者徐迟先生所说,在繁忙的白昼他有时会将信将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好处,直到黄昏,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来,才觉得"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肺腑,动我衷肠",而到夜深万籁俱寂之时,就更为之神往了。
那么,为何要扰它?扰这寂寞?
梭罗是个法国血统的美国人,只活了四十五岁。他的挚友,年长他十四岁的爱默森在他死后曾对其人格特征作过一番栩栩如生的描述:梭罗喜欢走路,并认为走路比乘车快,因为乘车你要先挣够了车费才能成行。再说,假如你不仅把到达的地方,而且把旅途本身当成目的呢?但他几乎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及其附近的山水。
他觉得他家乡那块地方包含着整个世界,他是能从一片叶子就看出春夏秋冬的人,他家乡的地图就在他的心里,那地图自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固定的,而是活动的,云会从它们那儿带走一些东西,风又会把它们送来。
他曾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哈佛)受过教育,他也曾到当时荒凉的瓦尔登湖边隐居,像一个原始人那样简单地生活,他想试试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够简单到什么程度,想试试用自己的手能做些什么,他用很短的时间就动手造好了一个颇能遮风蔽雨的小木屋,这说明住房困难其实不难解决,即使胼手胝足用最原始的方式。
如果我们现在变得这么难,那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他曾经试制过一种新型铅笔,可是,在这铅笔真的可以为他带来利益时,他却又不想干这营生了。
试制成功了对他来说就等于说事情干完了,大量生产而牟利并不是他的事。他生前也出了几本书,当时都并不引人注目,他遗下的日记却有三十九卷之多,里面自然有一些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不过,他这个人确实挺有点意思,还有他那个湖。
梭罗性格中最吸引我们的可能就是那种与我们的性格最不同的东西,就是他整个人的独特性。他也许比别人更多地逃脱了概括,逃脱了归类。梭罗生活得有时像个隐士,他可能时常觉得那山、那水比那人更与他相投,山川草木均是他的密友,甚至他的一个朋友也说他:“我爱亨利,但无法喜欢他,我决不会想到挽着他的手臂,正如我决不会想去挽着一棵榆树的枝子一样。”
真的,他生活得像一棵树——我们可以从树的全部意义上去理解这句话:它的伞样的形状,它不断迸发的枝条、它的蓬勃向上、它的扎进土壤深处的根须和承受阳光雨露的绿叶,尤其是它的独立支持和独立性,对于梭罗,我们可以像惠特曼一样说:
在路易安那我看见一棵活着的橡树正在生长,
它孤独地站立着,有些青苔从树枝上垂下来,
那里没有一个同类,它独自生长着,
发出许多苍绿黝碧的
快乐的叶子。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说,这树又不是孤独的,寂寞的、与世隔绝的。它与世界的联系和作用是通过它隐秘而深刻的根须、通过大地进行的。通过大地,它不仅和它的同类,其它的树木联系着,也和青草、鲜花、阳光、雨露和整个大自然联系着。
联系干吗非要互相蹭在一起?"人的价值并不在他的皮肤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碰皮肤。"不要模仿,而是表现你自己的独特性吧,你才配得上你的称号——人,你才可能和其他人发生一种真正的联系,才可能和真正伟大的大全和唯一发生一种联系。
世界上有多少个窗口,就有多少种生活,所以,命题小说虽然难做,以“窗口”命题倒还不失为一个补救办法,就像前不久有人试过的。我们在大街上闲逛,特别是新到一个地方,有时会对某些窗口发生好奇:那里面在进行着什么呢?他们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呢?想来会和我们有些不同。有的窗口对这种好奇心是敞开和欢迎的,有的窗口则在黑黑的帷幕下摆出一幅莫测高深的面孔。
这是站在窗外,调换一下,站在某个临街的窗口里面,我们有时也会注意底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凝视着某个我们感兴趣的面孔,她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时我们自己的生活过腻味了,我们更想知道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另一些人,他们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
比方在契诃夫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想法变成了一种渴望、一种非常感人的东西,这正是契诃夫魅力的一个秘密。也许,正是这一种渴望和好奇,提供了我们第一节提出的问题的部分答案。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追求完美的艺术家,有一天他想做一根手杖,他想,凡是完美的作品,其中时间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自言自语,哪怕我一生中不再做任何其它的事情,也要把它做得十全十美。他一心一意,锲而不舍,目不他视、心无他想,坚定而又高度虔诚,在这整个工作过程中,他的同伴逐渐离开了他,都死去了,而他在不知不觉中却保持着青春,最后当手杖完成时,它突然辉煌无比,成了梵天世界中最美丽的一件作品。
做好一件事,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专心致志于你所做的事,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要急于成功?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伙伴,那也许是因为他听到的是生命的另一种鼓点,遵循的是生活的另一种节拍。
人啊,不要用世俗的成功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人吧。而你却要专心致志做好你要做的事,一辈子也许只是一件事。
而这就要使你的心灵单纯。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简单,你要去弄清那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这往往是大自然慷慨提供给每一个人的。不要以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简单的问题,不要以多余的钱和精力去购买多余的东西。
读《瓦尔登湖》中梭罗的流水帐就像读一首诗。他计算了自己造那间小木屋的支出,总共是花了28块1毛2分5;他也计算了他在一段隐居期间的饮食费用及其它支出,得出了收支相抵后的差额。我觉得,读这些看来枯燥的数字就像读一首诗。梭罗的手不仅拿笔,也拿斧子,梭罗的眼睛不仅看书,也看绿树、青草、落日和闪动着波光的湖水。他的脑子自然也在思考,是在接近思维之根的地方思考,在那里大概也埋着感觉之根、情感之根。
梭罗认为:美的趣味最好在露天培养,再没有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快活的了。说梭罗是"大自然的挚爱者"也许还不够,他常常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他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踏在地上的脚印常常是深的,那意示着一个负重者。他不把花从枝子上摘下来,但把汗洒进土里。
我们总是过于匆忙,似乎总是要赶到那里去,甚至连休假,游玩的时候也是急急忙忙地跑完地图上标上的所有风景点,到一处"咔嚓、咔嚓",再到一处"咔嚓、咔嚓",然后带回可以炫示于人的照片。我们很少停下来,停下来听听那风,看看那云,认一认草木,注视一个虫子的爬动。
我们有时大概真得这样,就像战时英国为节约能源而在火车站设置的宣传牌:“你有必要做这一次旅行吗?”我们要这样询问一下我们自己:“你有必要做这样一件事吗?”以节省我们的生命和精力。
人们总是乐于谴责无所事事,而碌碌无为不更应该受到谴责?特别是当它侵害到心灵也许是为了接纳更崇高更神圣的东西而必须保有安宁和静谧的时候。在梭罗于瓦尔登湖度过的第一个夏天,他没有读书,他种豆子,有时甚至连这也不做。
他不愿把美好的时间牺牲在任何工作中,无论是脑的工作或手的工作。他爱给他的生命留下更多的余地。他有时坐在阳光下的门前,坐在树木中间,从日出坐到正午,甚至黄昏,在宁静中凝思,他认为这样做不是从他的生命减去了时间,而是比通常的时间增添了许多、超出了许多。
美国的十九世纪被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独特的美国文化诞生和成长的时期,是继政治独立之后美国精神、文化从欧洲大陆的母体断乳而真正独立的时期。这一时期中以爱默森和梭罗等为代表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思潮尤其令人注意,爱默森的《美国学者》的讲演被人称为是“我们思想上的独立宣言”。
"超验主义"这一并不确切的戏称也许只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表现了这一思潮的一个特征,即崇尚直觉和感受,这一思潮更重要的意义是体现在它热爱自然,尊崇个性,号召行动和创造,反对权威和教条等具有人生哲学蕴涵的方面,它对美国精神文化摆脱欧洲大陆的母体而形成自己崭新独特的面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而梭罗比演说和写作更多地是实践和行动,在他的性格中,那种崇尚生命和自然、崇尚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和那种曾经在美国的开发,尤其是西部的开发中表现出来的勇敢、豪迈、粗犷、野性的拓荒者精神不是有着某种联系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哲学和著书立说联系到了一起,似乎非著书不足以立说,非立说不足以成为一个哲学家。可是,人们往往忘记了最早的哲学都不是写出来的,无论在东方、在西方。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哲学都只是门徒与后人对他们生活和谈话的笔录。而还有那些没有流传下来的呢?哲学是一种显示,有时是有意、有时是无意的显示,有时连显示都不是,甚至于是一种有意的隐蔽,那么,去注意人们的生活吧,要并不亚于注视书本。
梭罗也谈到过哲学,他说:“近来是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然而教授是可羡慕的,因为教授的生活是可羡慕的,但是,要做一个哲学家的话,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不但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而且要这样地爱智慧,从而按照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他做了他所说的,他比许多哲学教授更像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具有古朴遗风的哲学家。他不单纯是从书本中熬出一点学问,他贡献给我们的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梭罗还有另外的一面,这一面也许在《瓦尔登湖》中并没有明白的展示,但不了解这一面就不能完整地把握梭罗的性格。这一面即不是避世而是入世的一面,不是作为隐士而是作为斗士的一面,虽然不是约翰·布朗那样进行暴力反抗的斗士,而是作为主张非暴力反抗的斗士,但他的看法似乎比前者更清醒、更深刻,看到了问题的更深症结所在。
梭罗反对美国的奴隶制度,反对美国对墨西哥的侵略,他对人类社会中他认为是恶的东西的憎恨程度不下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曾因拒绝交税而坐过监狱(本文由慧田哲学推送),一八四九年他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公民的不服从》(作为单行本出版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被人认为是历史上改变世界的十六本书之一,他倡导的"公民的不服从"( civil disobedience)的思想对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印度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在他那里,有着某种隐士和斗士的奇妙结合。
十一
梭罗并不希望别人成为和他一样的人,因为他希望自己也不总是过去所是的人。他不执意要做一名隐士,他想隐居时,他就来了,他觉得够了时,他就去了。
他当然不会像李固《遗黄琼书》中指斥的那样以处士之名"纯盗虚声",他大概也不会像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那样壮怀激烈地谴责不再隐居的人。他注重的是生活得自由,而不是执着于某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
他明确地说他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他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出并坚持他自己的合适方式,而不要简单地因袭和模仿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生活方式。他是一个天生的倡异议者,对每一个建议本能的反应是说"不"。而现在有什么人愿意做人中的黄蜂呢?人们更喜欢在互相恭维的泥淖中打滚。
他的善意和同情并不表现为顺从别人,他的坚定和明智也不要求别人的顺从。他要自己绝对自主,也要每一个人都绝对自主。可是一个人仍然可以这种意义上成为和他一样的人:即成为一个与任何其他人(当然也包括梭罗)不同的人,成为一个可以说这一句话的人——
我是我自己。
十二
从一八四五年七月四日到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梭罗独自生活在瓦尔登湖边,差不多正好两年零两个月。瓦尔登湖不仅为梭罗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也为他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氛围。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这块地方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正匍匐的地方,但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出发去寻找它。它不仅是我们身体的栖所,也是我们心灵的故乡,精神的家园;它给我们活力,给我们灵感,给我们安宁。我们可能终老于此,也可能离开它,但即使离开,我们也会像安泰需要大地一样时常需要它。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曾如此谈到这种心灵故乡的意义:
“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客;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同小伙伴游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衢,对他们说来都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宿站。这种人在自己亲友中终生落落寡合,在他们唯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孑身独处,也许正是在本乡本土的这种陌生感才逼着他们远游异乡,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说不定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隐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习性和癖好,叫这些彷徨者再回到他们祖先在远古就巳离开的土地。
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会神秘地感觉到这正是自己的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在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安静。
”
而梭罗是幸运的,他出生的地方就是他精神的故乡。不过,从他的祖先是从法国古恩西岛迁来而言,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寻找,一种失而复得。谁知道呢,也许他更其遥远得多的祖先(梭罗决不会以自己是美洲士著的后裔为耻的)曾冒死漂洋过海,而现在梭罗又重新找到了他的故乡。
十三
世人不断致力于占有更多的东西,梭罗也另有一种奇特的占有;世人纷纷地购进卖出,梭罗也另有一种奇特的购买方式。在他看来,如果你喜欢某处庄园,喜欢某处风景,你不必用金钱买下它,在它里面居住,而是要经常在心里想着它,经常到它那里去兜圈子,你去的次数越多,你就越喜欢它,你就越可以说是它的主人,就像一个诗人,在欣赏了一片田园风景中的最珍贵部分之后就扬长而去,那庄园主还以为他拿走的仅只是几枚野苹果,诗人却把他的田园押上了韵脚,他拿走了精华,而只把撇掉了奶油的奶水留给了庄园的主人。
这种购买付出的不是金钱,而是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它付出的是一颗挚爱的心,还有体力,它得到的自然也更珍贵。这种占有是不为物役的占有,也是一种不妨碍他人占有的占有。
瓦尔登湖,我没有去过,不知道那是怎样一个湖,不知道它今天是否变成了某一个人的产业,可是,我们不总是可以在前面的意义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