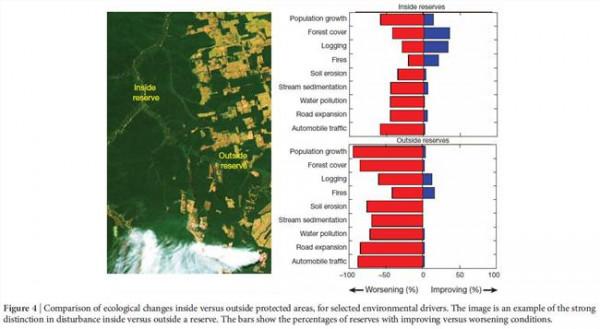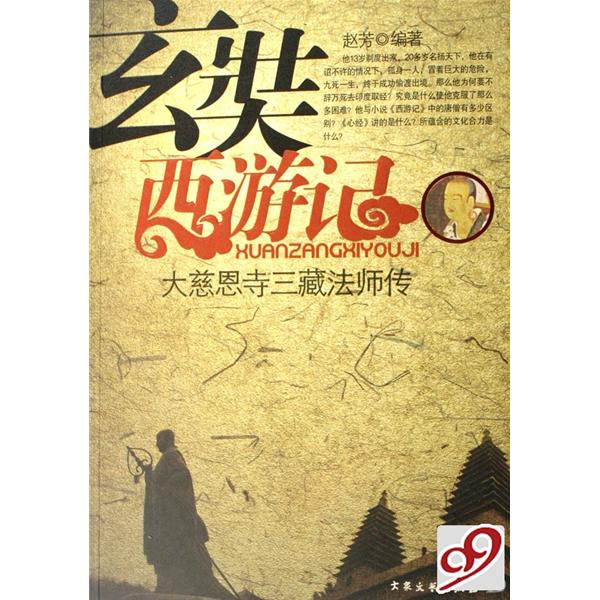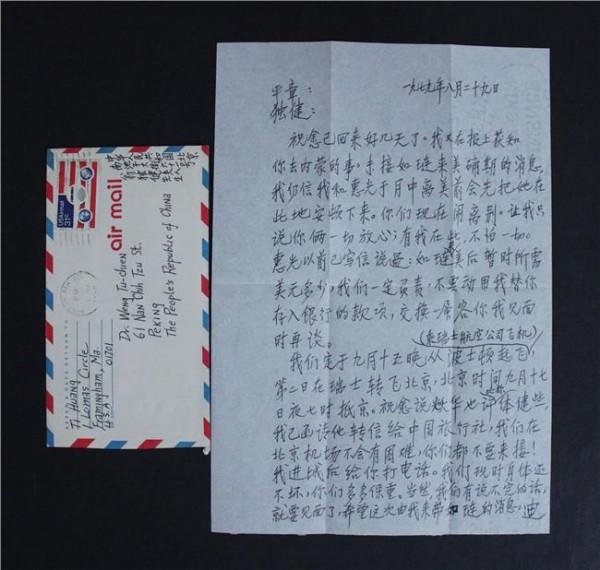【什么是生物学】生物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20世纪50年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这和信息科学的诞生在时间上如此巧合,信息科学中使用的一些术语,如程序、编码等,后来都在遗传学中利用上了。当前人们似乎认为分子生物学已经到了“最后开花结果”的阶段了。

须知,分子生物学的真正目的不在于创建能够在地球上生活的一些新型生命类型,以便为人类提供高质且数量充分的产品;分子生物学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基因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来揭示人类、动植物的生理过程,以及细胞分化,胚胎发育,生长、衰老直至死亡的全过程。

就是说,要对生命时间阶梯的机理按正确顺序进行全方位追踪。即便生命本身现在仍然是一个奥妙无穷、深不可知的秘密,可人们一旦将他们和分子联系,进行综合分析,那么就有可能接近其终极秘密了。

因此,人们主张先不考虑生命是否已知或未知,我们抄近道,直接来认识生物分子——看来这可能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在进行这类研究时,可以考虑研究分析逐级爬升的生命时间阶梯的结构,这样就能够认识愈来愈复杂的生命过程。
生物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人类自身,弄清楚人类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把构成自己知觉和个性特征的物质基础弄清楚。其实,人类对自己的大脑知道得太少,例如神经解剖还十分粗略,神经生化只有零星资料,更不用说有关信息的贮存、加工、提取等一系列活动的机理了。
过去的200万年,人脑体积增大了3倍,其中负责计划、决策的大脑新皮层增大明显,大脑的信息贮存量却很难估计。这些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实早在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立体结构模型后,德尔布吕克就曾预言过:“双螺旋及其功能不仅对遗传学而且对胚胎学、生理学、进化论甚至哲学都有深刻影响。
它对现代人的深远影响莫过于几乎人类的一切性状都可能有部分的遗传学基础。这不仅限于各个人的体质,而且还包括智力或行为特征。遗传素质对人类非体质性性状,特别是对智力的影响正是目前争议最多的生物学与社会学问题。”
2013年,美国还公布了脑科研计划,以探索人类大脑的工作机制,绘制脑活动全图,并且最终开发岀针对大脑不治之症的疗法,此计划启动资金1亿美元,可与人类基因组计划媲美。此项计划由瑞士洛桑理工学院的亨利·马克拉姆牵头,并由87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研发团体承担任务。
目前中国学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原院长饶毅现在的研究领域是“社会行为的分子和细胞机理”。美国有40多所大学、100多个课题组从事这一颇具前瞻性的研究课题,人们对未来充满好奇。
生物学不仅要研究人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还要研究人的本质以及他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当然这还要借助其他学科,这几乎将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且包括人类自身的种种尝试。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活动,但在漫长征途的苦苦跋涉中,人类无法规避这些活动。
那些第一代分子生物学家都早早地转向神经分子生物学前沿去开拓道路了,随后进入这一领域的不乏他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过去物理科学、化学科学和生命科学之间实现过富有成效的互动,使得在分子遗传学和免疫学的精确知识方面取得突破,即解开分子密码,今天这种互动在了解人的神经系统方面看来有可能取得相似的突破性进展[152]。
神经分子生物学一个最重要的技术发明是光遗传学,就是用光来操纵分子。我们只要沿着现在的研究思路走下去,做更多的实实在在的研究实验,就是下一个突破口所在。
恩格斯早就预言过:“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里发生的分子和化学的运动[153]。”恩格斯预言的那一天不就是综合了各学科、各个领域研究成果的总和吗?到时候,只需在相应的表格上打几个钩就能实现,像组装电脑那样方便;研究开发人的大脑潜质,因材施教,推进DNA编辑技术。
人类还可以模拟人类大脑中全部860亿个神经元,以及将这些神经元连接起来的100万个神经突触的功能,到时候,可以建成一个“即插即用”的大脑,可以把它拆分,找出脑部疾病的原因,也可以借助机器人技术,开发一系列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甚至还可以戴上一副虚拟现实眼镜以体验“另类大脑”的神奇之处。
我们错失了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但抓住了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机遇,让我们伟大的祖国跃升为工业和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但是,现在面临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选择,而第六次科技革命很可能是在生命科学、物质科学以及与它们交叉的领域出现。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内容和发展有以下五大学科:
(1)整合与创生生物学,可解释生命本质;
(2)人格信息包技术,包括人脑的电子备份与虚拟再现;
(3)仿生技术,即人体仿生备份和躯体仿真;
(4)创生技术,包括创造新的生命形态和生命功能;
(5)再生技术,生物体的体内体外再生。
由此可见,上列五大学科在很大程度上都涵盖了生命科学的内容,正像诺贝尔奖诸多奖项中,生理学或医学奖固属生命科学范畴,而化学奖中获得诺贝尔奖的从1901年以来,截至2018年,共颁发了110次,有180位获奖者,但其中一半人次是因为生命科学、生物化学的内容而获得诺贝尔奖的。
老一代分子生物学家,亦即那些用生物学概念来解释大肠杆菌及噬菌体的一代宗师,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先用综合意义上的学说形式,提出自己的概念,在有了实验数据后,他们的这些概念才会被人们接受,再经过实验检验,但从中仍可能找出有某些片面性或不完善之处,这是一切概念、学说和理论可能都会存在的问题。
但是概念也好,学说也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标上了时空条件限定的烙印。现在这些老一代分子生物学家皆先后作古了,以原核生物作为研究材料的黄金时段,也跟随他们一起走进历史。
他们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认识到,决定大肠杆菌及噬菌体遗传性状的基因数目有限,只有将真核类生物的染色体结构和功能一步步地搞清楚了,将基因的结构和功能搞清楚了,才能再来揭示动植物乃至人类的生理过程,以及细胞分化,胚胎发育,生长、衰老直至死亡的全过程。真核生物比原核生物更加复杂,研究难度更大。
以后的科学史学家如何叙说我们今天的生物学呢,他们在研究我们现时的历史时,在有些事情经过若干年后,他们会从中判断出我们正在错过的或被我们低估了的力量倾向和趋势。爱因斯坦知道牛顿那时尚不知道的一些事儿,今天我们知道爱因斯坦那时尚不知道的一些事儿,明天的人将知道我们现在尚不知道的一些事儿。
对于科学史学家而言,无论修史、治史,还是教史、读史,倘若大家都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就恐非所宜了。修史、治史、教史和读史徒知事实,无补于全局。善修、治、教和读史者,观既往之得失,以谋将来之进步,于全局有利。在博大精深的科学论说史这类历史遗产面前,学以致用、引以为鉴,只是研读科学史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意义。一个真正的科学史研究者不仅要鉴史,还要鉴人、鉴事、鉴细节。
说到底,就是要鉴出什么样的时空条件、什么样的知识背景等诸多要素同时被激活、启动,才能迸发出灵感的火花,让思维发生质的升华。细碎处的故事、空白处的讲述,才能真正反映历史的原貌。我们站在50年后的今天,追忆50年前的一幕幕情境时,会很自然地与书中那些科学先驱们感同身受:时而为他们与DNA分子仅有半步之距,终因一念之差失之交臂而惋惜;时而又为他们向着DNA分子步步逼近,眼看就要成功而欢呼雀跃。
我们在不经意间享受到乐趣,在无意中营养了身心,这未必不是一种读阅科学史的优雅心态。读史还可以得到心灵的慰藉,让心灵充实,不惧黑暗,让人淡定、独立。
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马赫(Mach,E.)通过实验得出了气流的速度与声速的比值,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马赫数,以Ma表示,Ma=1126 Km,就是340m/s,汽车跑不了这个速度,大多数情况是用来表示飞行器的飞行速度。
用爱因斯坦自己的话说:“马赫才真正是广义相对论的先驱。”他早在1872年就曾告诫他的徒子徒孙们,“要寻找启示,只有一个办法—— 学习历史”。他的这套认识论科学哲学思想对当时的科学界一代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普朗克、爱因斯坦早年都是马赫思想的信仰者,约尔丹(Jordan,M.
E.C.)、玻尔、海森伯格、薛定谔、泡利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马赫思想的影响[86]。时过百余年,他的这番话对当今的生物学家或许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昨天意味着什么?17世纪有了经典力学,18、19世纪有了电磁学,20 世纪有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建立。如今21世纪可能意味着什么?或许是生物学世纪?明天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思考过吗?
摘自《DNA是如何发现的》,吴明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