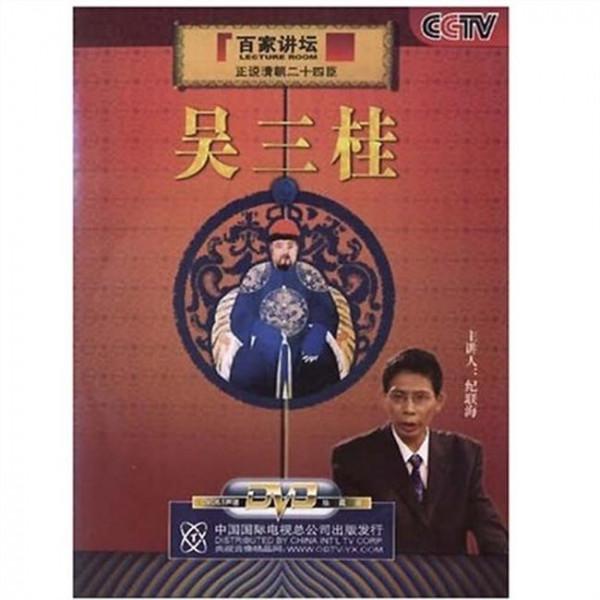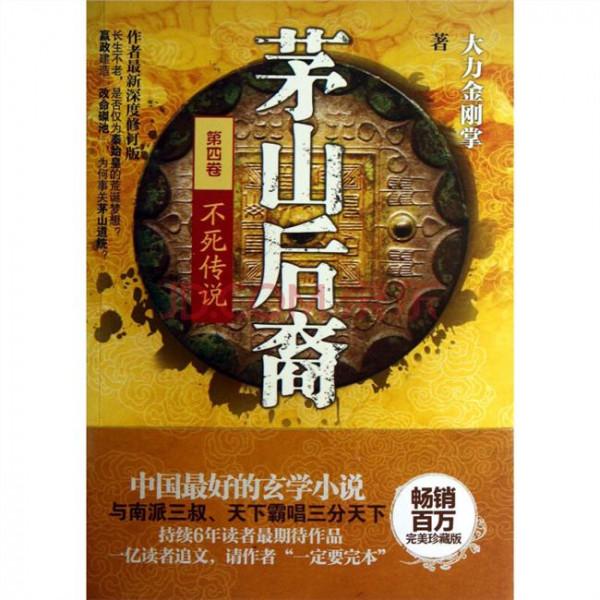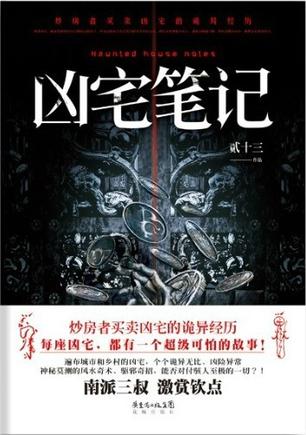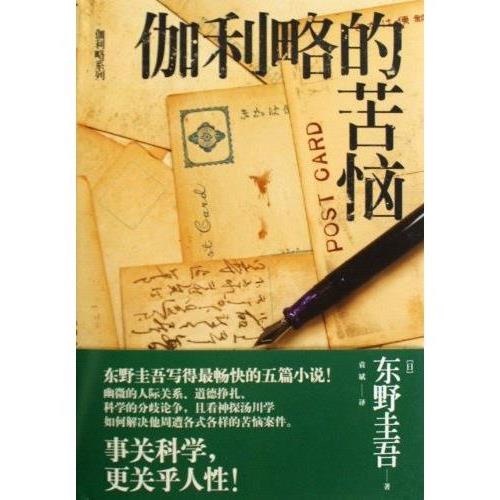【叶永烈有声小说】叶永烈:在漕溪路打开属于自己的天地
叶永烈的父亲叶志超曾任温州一家银行行长和当地医院院长。他的岳父杨悌曾任国民政府的温州军政府执法部副部长。叶永烈和妻子杨惠芬的少年时代,起居宽敞。他们不必操心家务,直到1964年,他们俩来到上海,住进12.3平方米的竹木简屋,一切要从头学起。

这是两人婚后第二年。叶永烈的妻子杨惠芬从温州调入上海一所中学任教。结束两地分居状态后,两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家。叶永烈此时已经从上海电表仪器研究所调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厂担任编导。他轮不到福利分房,当时月收入不过50元,租房每月要支出10元,数额巨大。

机缘巧合,一日两人在等43路公交车时,看见电线杆上贴着广告。打听之下才知道,漕溪一村567号,一位守寡的老工人决定卖掉房子,去女儿家住。这是半间私房,水泥地,上有一间阁楼,铺着地板。除了正面墙是砖石墙之外,其余三面是竹篱抹着石灰。虽是陋室,能挡风雨。他们随即以530元的价格买下。他们在这里真正开始恋爱,一住15个春秋,诞育两个孩子。他们用在这里学会的上海话,融入了上海的生活。
叶永烈夫妇居住15年的小屋
1979年,叶永烈分得一套两室一厅新公房,新居室离开漕溪一村不远。如今,夫妇俩又自购房屋,依旧不愿远离漕溪路。
为的,是一份情结。
从斜土路到漕溪路
温州人叶永烈,之所以会在上海的漕溪路安家,是因为当时工作单位的缘故。
从北大化学系毕业后,叶永烈被分配到上海电表仪器研究所工作。但在大学期间,叶永烈就作为主要作者写出了《十万个为什么》,还完成了《小灵通漫游未来》。此时的他,实在无心电表仪器,而是渴望继续科普创作。到上海一个月后,他就如愿被调入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厂。而这家电影厂,正位于斜土路2567号。
叶永烈在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厂厂牌前
1963年的斜土路,在叶永烈的记忆里,“不是现在的柏油马路,而是用花岗石块铺成的高高低低的弹硌路,人称‘又斜又土’——虽说斜土路因斜桥至土山湾而得名。斜土路很长,也颇荒僻,马路两边大都是用涂了沥青的黑色竹篱笆围起来的工厂,不见百货商场,也没有像样的高楼。”
1964年,妻子来沪后,两人以斜土路为圆心找房子安家。不远处的漕溪一村567号的这间平房,位于漕溪路东侧,成为两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家。
叶永烈考证过,这些简陋的平房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那时,填平徐家汇的臭水河──肇嘉浜,河边棚户的居民迁到这里。这里新盖了一批简易平房,原先说作为过渡房,几年后另迁他处新居。可是,后来由于经费短缺,这些过渡房竟成了永久房。
平房构成一条条弄堂,每条长约200米,中间是一条五六米宽的弹硌路。平房的门前有一米多宽的青砖“上街沿”。弄堂这一头是煤球店、小菜场,那一头是公共厕所。弄堂的中点处是供水站,因为家家户户没有自来水,要用塑料桶凭竹筹子从供水站的自来水龙头放水、拎水。家家用马桶,每天,在环卫工人一声声“马桶拎出来”的报晓声中,一天算是开始。
叶永烈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厂厂长洪林
这片平房里,大多住着位于今徐家汇绿地的大中华橡胶厂的工人。面对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叶永烈夫妇,久居此地的邻居们,热情扮演了保护者和引路人的角色。
叶永烈的妻子起初不会用煤球生炉子,是邻居手把手教会她:先用报纸引燃,再放柴爿,再放煤球。他们教会她,如何熄灭火舌又保留火种,到做饭时再轻轻一转,把炉子烧旺。邻居们也教会小夫妻凭筹子到家对面的老虎灶打开水。到了星期天,夫妻俩和邻居们一起,围着供水站,两脚踩在脚盆里洗被单。听着大家一边洗衣服一边家长里短地聊天,这是小夫妻从未过过的生活,接地气且温馨。
老虎灶边上,就是菜场。许多老人买好菜,就到茶馆坐一坐。所谓的茶叶,不过是粗茶或者茶叶末,配上老虎灶老板卖的五香豆腐干、香烟、糖果、瓜子,老人们自得其乐。叶永烈坐在家里,能听到苏州话、无锡话、宁波话、苏北话,声声此消彼长,不断传进陋室。
虽坐屋中,如行闹市。为招揽下午场的生意,茶馆老板还请来评弹艺人说书,叶永烈出门一看,只见茶馆里桌桌满客。趴着听的客人、抽着烟听的客人、站在后排听壁书的小孩,构成一幅生活气息浓郁的画卷,从此一直留在叶永烈心里。
叶永烈在担任电影导演的时候
后来,这些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场景,被叶永烈写入长篇小说“上海三部曲”。
从轰动弄堂到离开弄堂
远离温州的家人,漕溪新村平房里的邻居成了叶永烈夫妇的新家人。
叶永烈记得,他的右舍隔壁是一对老夫妇,丈夫是木匠,妻子在里弄工厂工作。叶永烈夫妇喊他们“公公”“婆婆”。有时叶永烈的两个儿子放学回家,家里没人,他们就直接去公公婆婆家做功课。有一回,叶永烈到老夫妇家去,看到他们桌上放了十几把剪刀,在磨剪刀。原来两位老人收入拮据,于是替一家工厂磨剪刀补贴家用。
叶永烈的左邻人家,两代都是工人。在非常时代,叶永烈遭受冲击,老工人挺身而出维护叶永烈,还经常说宽心的话,替他鼓劲。叶永烈家右边的一户邻居,是一位兰州大学退休的女教师,新中国成立前是联合国译员。终身未婚的她喜欢孩子,总是招呼叶永烈的两个儿子去玩,在幼儿园教语录歌的时代,她却教两个孩子英语。“文革”结束后,叶永烈有一次遇到一位老先生出现在女教师家,原来他是她在联合国工作时的男朋友。
叶永烈隔壁过去二户人家,算是弄堂里最宽裕的家庭,家里有一台24英寸黑白电视机,被孩子们称呼为“电视机阿姨”。1978年的一天晚上,“电视机阿姨”急急忙忙跑进叶永烈的家,大声呼喊“快来我家看电视”,拉起叶永烈夫妇往她家跑。原来,电视里正在播出叶永烈的专访,是上海电视台女导演富敏率摄制组来叶永烈家拍摄的。弄堂里从未见过拍电视,更未见过熟人上电视,一时之间,叶永烈轰动了整条弄堂。
1980年3月叶永烈导演的《红绿灯下》荣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
在这样的环境里,叶永烈出版了10本书。1978年底,《光明日报》记者谢军到叶永烈家采访之后,写了一份内参提及:“他创作条件很差,一家四口人(大孩12岁,小孩8岁)挤在12平方米的矮平房里,一扇小窗,暗淡无光,竹片编墙,夏热冬凉,门口对着一家茶馆,喧闹嘈杂。
每年酷暑季节,他就是在这样的斗室里,不顾蚊虫叮咬,坚持挥汗写作。”内参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批示。1979年6月,叶永烈所在的上海科教电影厂通知他,上海市政府特意分配一套建筑面积4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新房,以改善他的居住条件。
消息一出,整条弄堂再次轰动了。
邻居们用一辆“黄鱼车”帮助叶永烈来来回回搬运家具和书籍。这次搬家后,新房还是在漕溪新村。之后每年春节,叶永烈全家前往老房子给“公公”“婆婆”及老邻居拜年。那些年里,女教师也常来他的新居坐坐。
别了,陋巷里那12.3平方米的空间。如今,平房老宅虽然已经拆除,但它像屋角的第一块基石一样,见证叶永烈夫妇在异乡上海打开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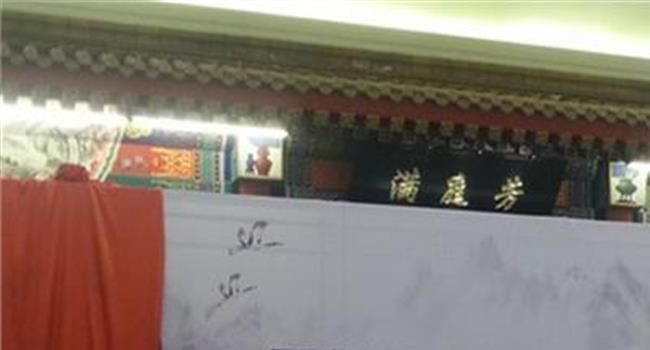


![东周列国故事[曹灿][有声小说]](https://pic.bilezu.com/upload/b/f3/bf3492eec3070ee96a015f0ca588272c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