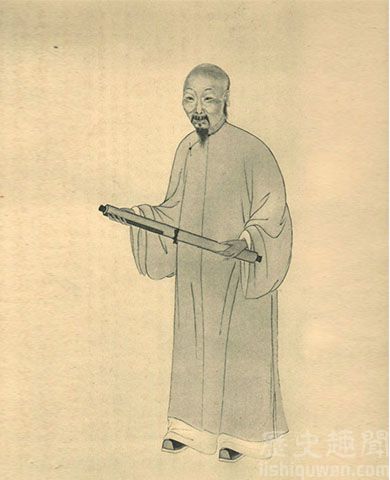侯方域桃花扇 侯方域:桃花扇底是流离
去年冬天,正遇降温,我被一阵北风卷进河南商丘。叶落中原寒冬,满地霜冻。
商丘人建造了翡翠楼那样的假古董,想证明李香君随夫归故里。李香君到底在南京栖霞出家,还是以侍妾的身份住进商丘侯府,一切都扑朔迷离。

又有好事学者们著书立作,争辩侯方域在顺治八年参加清朝科举考试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此事也是莫衷一是。
后一件事不重要,真相就是侯方域确凿无疑参加了那次乡试。参加乡试就算是“降清”、“仕清”了?也许是上有高堂,如果不应乡试就会株连父兄,或者是正逢壮年不甘以前朝遗民的心态了度此生,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官宦之家,自小接受正统儒家教育,不得功名,枉为男儿。

前一件事反倒成了永远的谜局,种种关于李香君随夫归乡的野史传闻都不足以为信。由于李香君的名妓身份,侯氏家谱里不可能有记载。侯方域著书数十卷,提及李香君的仅寥寥数笔,而所撰的跟李有关的一切文字里也没有提及她的归宿,更难寻觅有关爱情的痕迹。

对于一个中国古代的正统士大夫来说,著作中不过多涉及妻妾也属正常,仕子们岂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但是疑问来了,李香君在侯方域的生命世界里真的那么重要吗?文学作品《桃花扇》改造了作为历史人物的侯方域,孔尚任的《桃花扇》用名士的浪漫风流掩盖了人生的流离悲苦。李香君会不会是侯方域生命中的一个凄美的音符,而孔尚任却把一个音符扩写成了全部乐章?

都说女人爱慕虚荣,公正地说,其实更贪恋虚荣的是男人。女人要的也就是几件光鲜衣衫和名贵首饰,男人要的是空间上的疆域辽阅和时间上的青史留名。政治能满足男人的虚荣心,政治宏伟,政治高深,政治肮脏,总之政治诱惑男人。
为了政治,一朝又一朝,上上下下的层层官员们都在忙碌着,官场上,从来都显得那样的浮躁不安。
男人容易被女人诱惑,男人更容易被政治诱惑。政治里有功名,政治里有权力陶醉,政治里有理想与抱负,政治里有“力比多”生命力的释放。
侯方域是拥有健强的“力比多”生命力的男人。14岁,一般人尚为懵懂未开的顽童,而侯方域却以少有的大气吟出“自居风霜气,终非燕雀情”的句子,大气磅礴啊,其超人的文学才华及高远的宏图大志跃然欲出。文学上是正宗的儒生见地,主张以《诗经》的风雅之道为宗旨,以盛唐的杜诗为典范。
侯方域也是典型的受政治诱惑的男人。少年时随父游京师,才名播于公卿间,青年时代金陵赶科场,主盟复社成为首领,继而返乡组建雪苑社,他主持的那些文学活动本质上也是政治活动的一种依托。再回南京,抨击阉党,议论朝政,遍交江南名士,指评当世人物,一派雄视当世,舍我其谁之意。
舍不得上前线杀敌,索性就在身边“杀敌”,与阮大铖不共戴天,为躲避阮大铖缉捕,漫游嘉兴流散苏州。这些政治较量的同时,大明江山也在党争与清谈的喧嚣声中加速崩塌。
甲申之变李自成起义攻破商丘,侯氏一族二十余人死于劫乱。不久,侯方域再遭阉党追捕而入扬州史可法军中,又被推荐为徐州高杰军监纪推官,随高杰北上抗清,亲历战局。生逢乱世,人如草芥,时代风云激荡,江山万里尸骨,而这位侯公子关注世事的豪情不减,在挽救大明王朝的政治疆场上挣扎,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说什么复社领袖,说什么倜傥才俊,他侯方域现在的模样就是一个混迹在逃难潮流中的瑟缩书生,在乱世的死人堆里滚爬。
欲想激浊扬清,世道越激越浊,越搅越浑。
要改朝换代了,生命是喋血的史诗,在政治的浊流中颠沛流离,桃花扇底藏着的不是风流婉约,是一生的流离啊。情爱只是冗长压抑史诗中一小段舒缓的过渡。为政治而科考,科举如重负,一旦失利,更加愁肠百结,更何况是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的末梢,科举应试就算金榜题名命运也照样绝望无常,纵酒狎妓成为缓解紧张的一种方式,这也就有了明末“嫖妓不忘忧国,忧国不忘宿娼”之说。
正是在这种任性中,遨游于金陵佳丽之地,驰骋于诗酒声色之场,复社公子侯方域自然也不能免俗,只不过,他遇到的是秦淮八艳之一的李香君,在胭脂香粉中找到了自己的知音,铁骨铮铮、漠视权贵、知情明理。
把才子佳人的生离死别置放在江山之恨、故国之思的浓烈底色上,这是孔尚任唯美的技术处理,桃花扇底送南朝,悲凉啊!
带着李香君“不复歌”的承诺,侯朝宗就这样一去不回。那时他不出22岁,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已过了大半。而据他的《与田中丞书》中的表述,他与李香君自桃叶渡别后已“不复更与相见”。李香君的故事和她的歌声一样,随着侯的离开而结束了。至于后来是不是被侯公子接到归德老家,只有天知道了,反正,昔年别君秦淮楼,冷香摇落桂华秋,侯方域的书文中未曾再提起这位薄命红颜。
侯方域的生命终止于36岁。残年的心境凄凉悲惨,万般滋味。天翻地覆,物是人非,兴亡之感,黍离之忧,修建壮悔堂,著《壮悔堂文集》,悔功业无成,悔壮志难酬,悔年华流逝,对自己不保名节参加顺治八年乡试一事,更是耿耿于怀,乡试之后,痛悔失足,抑郁自责,积郁悲伤。
旧时的相识,战亡的战亡,自绝的自绝,归隐的归隐,削发的削发,俯首的俯首……自己蛰居乡园,然人生多舛,终无法远离世事困扰而独承难言之隐,心境尤为复杂,每每忆及江南的往事故人,更是惊心溅泪,悲愤难抑。烟雨南陵独回首,侯方域和江南士子们所效忠的大明以及他们发誓不与合作的大清,一切都过去了,都化作了云烟,化作了虚无。
记得在他上下求索的青春年月,他和他的同仁们痛惜而追随的那个大明江山已经腐败溃烂之至,官场风气恶劣,王朝无力回天,而之后一帮明朝官僚拥戴的南明弘光小朝廷更是荒谬绝伦,又有多少历史与天道的合法性,一样党争不断,内讧不已,搜刮掠夺,无意抗清。
而江南士子们一定要为这个王朝誓死捍卫、竭尽忠诚,仅仅因为这个王朝姓朱?或者是汉人统治的王朝?其实,明王朝并没有给侯方域多少实惠,他的父亲虽说做到了户部尚书,但到后来被冤枉下狱,一蹲就是六年。侯方域纵然是满腹才华,但他面对的科举道路竟是如此的无奈与尴尬。他两次应试本应都是名列前茅,但一放榜就是名落孙山。他因参加复社反对阉党余孽阮大铖而几欲被杀。
想起那个时代的两个政权,一个割裂了宋以后就若断若续的文化命脉,一个弊政百出民不聊生,据说现在的各个历史论坛上明清之争硝烟弥漫。我无意做历史学家,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想,这争论的本身不就说明,即使是后世的我们,都不能肯定到底该做怎样的选择?
政治比人道更重要吗?政治比天道更重要吗?政治比人心更重要吗?
佛教里说,我执,法执。“我执”指对自己身心的执著,“法执”指对于事物和现象的执著。这些书生们执著于自我,也执著于世相。
抵抗要看情势吧,投降也没有什么不对呀?天险山海关挡不住关外的战马,何况这道已经脆弱不堪的扬州城墙?史可法顽守城池,激发的是清军更疯狂的报复,扬州十日屠城,生灵悲嚎,大地一片焦土。名节真的那么重要吗?扬州城妇孺的生命就不比政治更重要?守与不守,为生命还是为政权?
也难啊,真难啊。
眼见爱新觉罗家扫了中原,屠了江南,眼见堂堂列公蓄了发辫,着了异服。长江一线,吴头楚尾三千里汉家的江山,从此后归了别家姓,寒涛东卷,万事付空烟,只有冰冷的江风吹上满面纵横的老泪。再鄙薄功名的人,是硬汉男人,偏生容不得故土家园受糟践,容不得江山换主奴颜媚骨事异族。努尔哈赤的子孙啊,他们要知道,炎黄的子孙不会这么臣服在他们的马蹄之下。
这些执着于人间政治的书生中也有看得破的,比如冒辟疆,就悄悄领着董小宛隐居、退去。虽然隐居,清廷征召的文书却一封紧似一封,但他偏偏不出来。统治者的手里沾满了征服他族的鲜血,朝堂上列公脚踩着累累白骨,这个混乱喧嚣的天下,他只想躲进小楼成一统。
侯方域、冒辟疆,都曾是名满江南的风流名士,二人是“复社四公子”中的鼎鼎人物,当年满腹经纶,登高赋诗。在新的朝代中,老友们再也没有相见过,再也没有一块喝过酒、吟过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