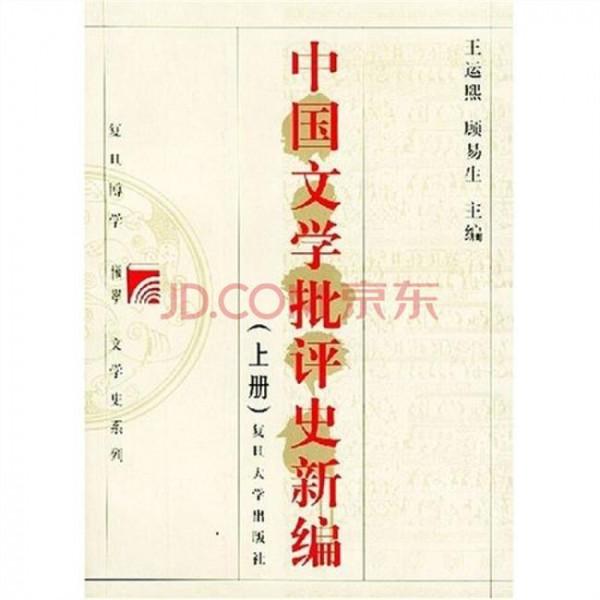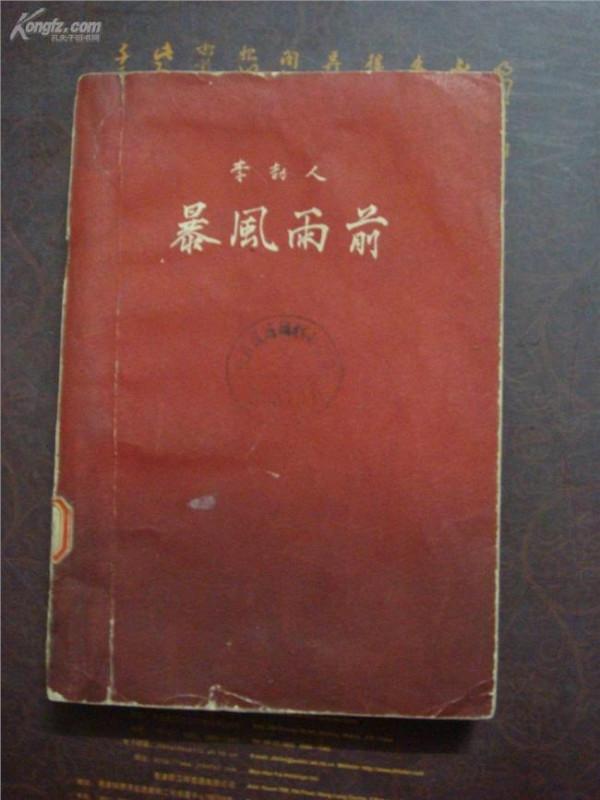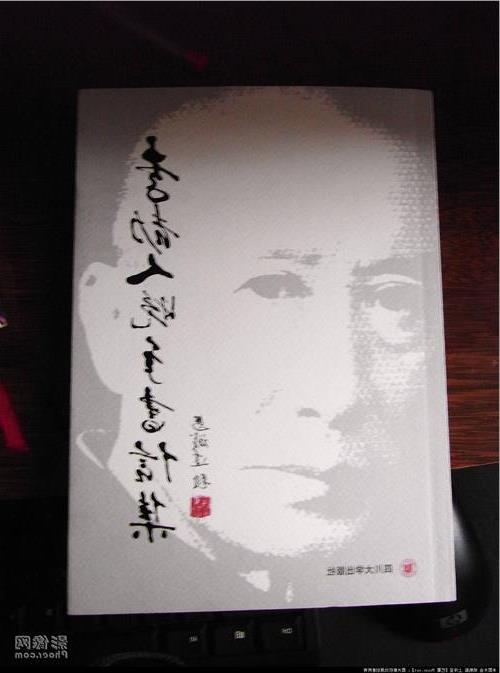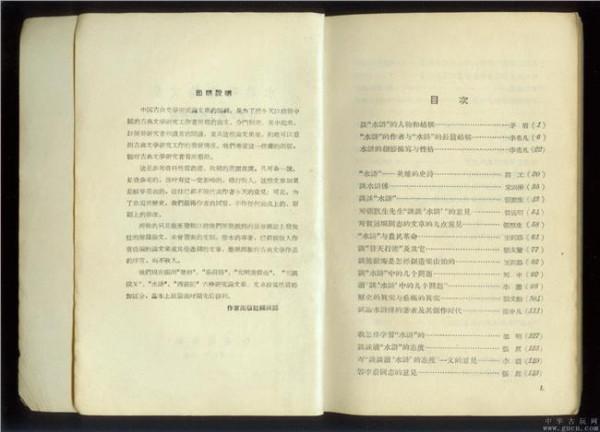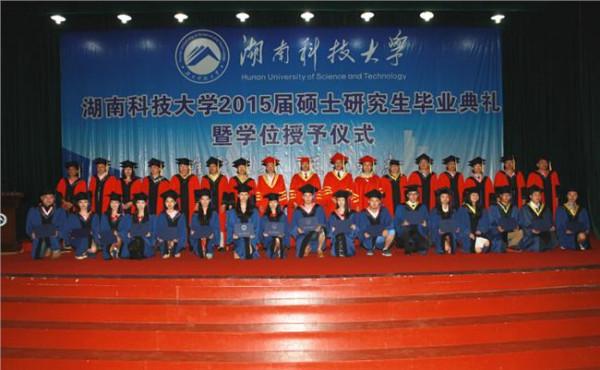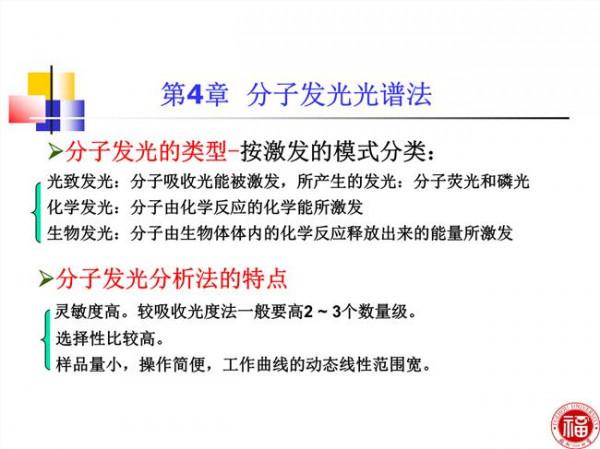吴越春秋上下李劼 吴越春秋(上下)(新历史文学系列)
自序 长篇小说《吴越春秋》 李劼 严格说来,用文字书写出来的历史基本上是文学的。文字书写的历史很难摆脱其与生俱来的文学性。也许孔子意识到了这样的困境,所以他修订历史的时候特别的小心。但饶是如此也难以免俗,或者说难以摆脱历史那种文学性的纠缠,要不然,就没有春秋笔法这一说了。
可见,小心翼翼修订历史的孔夫子,到头来非但逃不脱历史的文学性,或者换一种说法,主观性,而且还让人感觉他很世故很狡猾,明明带着自己的好恶,还要装模作样地做得好像十分客观,像真的一样。
相比之下,司马迁由于受了冤屈,反而成了个性情中人。司马迁写史,非但不避讳其文学性,而且大肆发挥其文学性,结果,《史记》比孔子的《春秋》更受欢迎,在人们的心目中好像更历史。
就是从题目上都可以感觉出来。史记的意思就是历史记载,而孔子那部装模作样的《春秋》反倒是十分可疑,因为首先,春秋一词就太文学了。假如作个民意调查,我相信读过《史记》的中国人肯定远远超过读过《春秋》的人们。
《春秋》是孔夫子编出来的,而《史记》乃是司马迁写出来的。在编出来的历史和写出来的历史之间,你说你喜欢看哪一种? 不过,窃以为,历史写到司马迁的份上,也该适可而止了。因为书写的历史虽然有着天然的文学性,但这种文学性一旦被滥用,也是很糟糕的事情。
比如后来的各种演义,就是历史之文学性被滥用的例子。可是,演义恰好又比《史记》那样的史书更受欢迎。中国人有幸通过大量的演义读自己的历史,中国人又很不幸地被大量的演义所塑造。
包括《三国演义》在内。 希腊人正好是个相反的例子。希腊人好像知道历史只能写到《伊里亚特》,《奥德赛》为止,所以他们没有演义。 中国人十分自觉地通过演义完成了自己的心理塑造。
演义有多么通俗,国人就有多么通俗,演义有多么粗俗,国人也就有多么粗俗。说国人乃演义中人虽然好像不太科学,但也八九不离十。再说,演义还不是最俗的,还有比演义更俗的。这里就不赘言了,反正国人大都心中有数。
我不知道该给自己的努力如何定位。我只知道我没有孔子那样的本事,但我比较认同司马迁那样的性情。虽然司马迁的《史记》比孔子的《春秋》有着更多的读者,但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或者说集体无意识的形成上,孔子的影响乃是十个司马迁都无法比拟的。
孔子的学说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把中国人牢牢地罩在其中。当然,也有些没被孔子所笼罩的,比如《红楼梦》所展示的精神世界。 我是碰巧从《红楼梦》里读出了被孔子学说笼罩以外的世界,然后再从那个世界朝上追溯到《山海经》时代。
我在《山每经》里,发现了中国人最为原始最为本真的集体无意识。假如有人问我,中国人原来是怎么样的?我的回答是,请读《山海经》。 不少国人,尤其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所谓红学家,为什么读不懂《红楼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读懂《山海经》。
没错,读解《红楼梦》得从中国人本真的休体无意识入手。这是《红楼梦》最为成功之处,也是其最难读懂之处。因为国人基本上被各种演义所塑造的。除了王国维,后来的红学家基本上是从演义甚至比演义更低级的层面上读解《红楼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