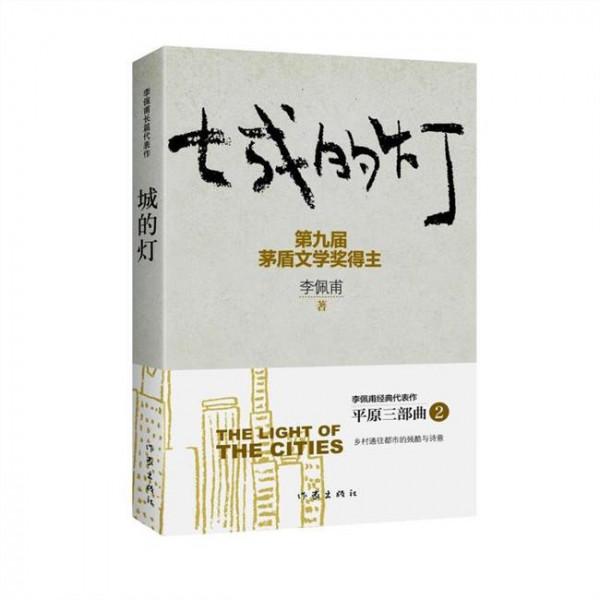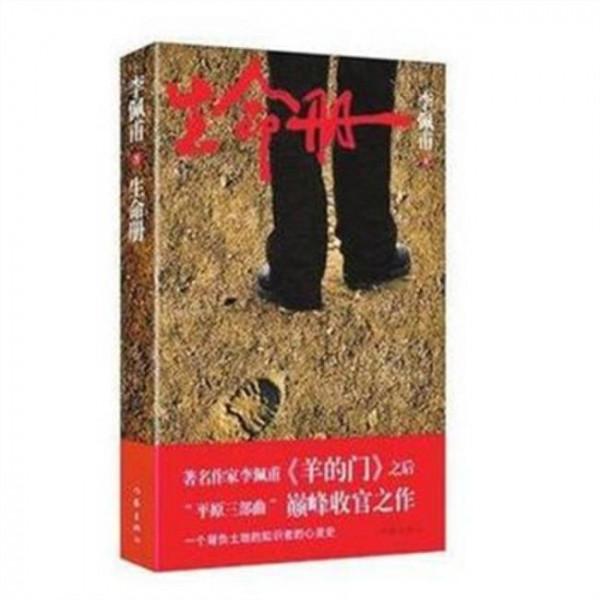城的灯李佩甫 李佩甫《城的灯》读后感
《城的灯》读后感 ---人民网人民书城 闵云童--- 作为一部以苦难和抗争为主题的小说,李佩甫的《城的灯》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围城"世界:城里有"荣光照耀",怡然而洁净;城外,则是一个巨大的不断为黑暗所吞食的黑洞,在欲望的渊薮中,罪恶肆意横行。
在这城里城外的相互纠缠、撕咬的阵痛中,李佩甫通过他笔下的人物给我们展示了生命在对苦难与欲望的抗争中所具有的厚重感,这种抗争也是他对生存境况与价值理想的一次更为深刻的反思。
在反思中,作者又一次提出的一个触及我们脆弱灵魂的极为尖锐的问题:我们的精神信仰归之何处? 李佩甫一直挚爱着他的豫中平原。在他的小说中,这片古朴的、具有浓郁乡村气息的土地却蕴藏着更鲜为人知的活力。
这活力往往不是在面子上显露着的,它是深藏于骨子里,随着血液的流淌行遍全身的;它不是锋芒毕露的,而是内敛的;它不是打开瓶塞就会飘香的酒,而是需要经年的窖藏的,愈埋愈沉默,愈沉默愈香醇。就因为这活力骨子里头是不屈的,所以它才不致于在沉默中消逝自己,而是以生命的潜流承载着人类的信仰之舟前行。
李佩甫笔下的人物则在这生命的潜流中默默地以抗争展示着生命的坚韧。在《城的灯》中,不论是为爱情而终贞不渝的刘汉香,还是为理想而放逐尊严的冯家昌,他们都成了生命力不断伸延而超越自我的佐证。
他们以沉默的方式选择了承受,在沉默中生命的张力被无限拉大。在这些人物身上,李佩甫所要表现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人性之美,更重要的是在他们潜意识中所板结的生命原冲动,这才是小说得以推进的原动力。
在豫中这块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土地上,唯有这生命的原冲动是亘古不变的,李佩甫所要传达给我们的正是这些。 李佩甫笔下的人物多富传奇性,他们因其意志的坚韧性与经历的不寻常性,越显出对生命体悟的深刻性。
可以肯定地说,《城的灯》中的人物无一不是在对生命进行着极具韧性的抗争。他们在苦难中塑造自我、超越自我,使自我与豫中--这块孕育着生命力的土地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他们与这片富于传奇色彩的土地的结合,使二者都在不觉中具有了极富力感的生命冲动。透过这些,我们能在史诗性的恢宏场景中去感受生命的力量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 《城的灯》对生命的感悟是多元而统一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冯氏一家的心路历程中找到踪迹。
冯家作为一个独姓家族在上梁--这个宗氏观念极强的传统村落,不断遭到排挤,最终他们被迫脱离了乡村文化母体而进入城市的空间。冯家在上梁所做的生存抗争的无力更显出了乡村宗氏文化对生殖与繁衍需要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
无视个体的生存,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性的逻辑,而上梁人却本能地接受着。在生存需要被宗族势力(权势)无情地驱逐之后,冯家昌选择了他全然陌生的城市。在这里,他必然又要面对巨大的城市神话对他的压抑,这造成了他身理和心理的双重错位。
他一步步地被纳入社会上层的轨道,并以此为起点规定了冯家五兄弟的前行之路,这是他们的堕落抑或是在寻找自我的救赎?似乎很难给以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种种文化观念的纠结中,小说所要展示的绝非是孰优孰劣的简单比较,而是要揭示由这种种观念所组合而成的生存境遇中存在的多元冲突。人活在这个冲突之网中,往往会成为一只身不由己的笼中鸟,难以突围。
李佩甫在小说中也引用了马克思的那句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与其说他是在重塑人的社会属性,不如说他尖锐地指出了人的一种悲剧性生存境遇:作为个体的我们是永远无法跳出这一窠臼的。 李佩甫在小说中选择了羔羊作为"城"的"灯",正暗示着他所赞同的个体在庞杂的社会关系网中所应坚守的道德立场。
正像他以冯家五兄弟在香姑坟前的沉重一跪作为结局一样,李佩甫依然执着地将他的精神家园定居在了诸如上梁的豫中大地之上。
经历过精神与肉体的分离、漂移和游走不定之后,最后终于求得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回归。较之《羊的门》,这显然是一次不小的突破。在《羊的门》中,呼天成身体力行地捍卫着一个乡村童话的尊严,在他抬起高昂的头颅时,一切城市的肮脏与官场的腐败就有如芒刺在背。
但这终究免不去一些自恋的味道。《城的灯》则更象是作者的一次精神漫游。在现实挫折的处处碰壁中,在潜在生命力的左冲右突下,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无寓更显突兀。在这种困境中,人不仅需要捍卫精神家园与坚守价值理想,更需要对生活本身的透彻体悟。
这体悟显然是伴随着痛楚的,它缘自与母体的距离日渐拉大,二者的分离过程就好像撕裂一个伤口,鲜血汩汩,却愈见症结之所在。这是李佩甫在创作中所具有的勇气,也恰是当下文坛所匮乏的。
作为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李佩甫似乎一直在寻找一个完美的、足以承载他信仰的载体,它须摒弃一切可憎与虚谎之举,须如羔羊那么纯洁,须能让他顶礼膜拜。他仿佛也曾多次以为自己找到了,所以他安排了《羊的门》中的呼天成,以及《城的灯》中的刘汉香,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在步履维艰的前行中夭折。
我们可以体会到李佩甫在艰难的前行中所迈出的每一步是何其沉重。然而正像他在开头引用的《圣经》所言,"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
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应算是一种精神的殉道,而唯其殉道,才能生发出更多新的可能。对于李佩甫追求理想的脚步而言,其作用大抵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