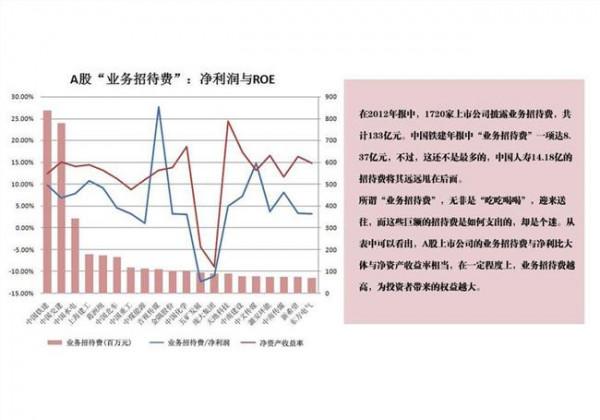【阿里巴巴招聘条件】10年 再造一个阿里巴巴
2018 年底,阿里巴巴密集举行了三场大的集团技术战略规划会议,讨论如何让技术体系更好地反哺业务,成为业务真正的驱动力。
讨论的最终结果,是将整个阿里巴巴的技术分为三类:统一于阿里云智能的底层技术;归属新零售技术事业群的贴近前端的技术;以及寄托着这家公司“技术梦想”的达摩院。

达摩院成立于 2017 年,但阿里巴巴集团技术战略部总监刘湘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 2014 年。
当时的阿里云已经基本解决了算力问题,王坚认为接下来的重心要转移到算法上。这需要成立一个类似研究院的组织。现在是阿里巴巴集团技术战略部总监的刘湘雯,此前她曾担任阿里云的销售,后转做技术传播和技术战略。 2014 年她和同事向马云汇报研究院的计划时,马云想出了这个名字。

像“登月计划”一样,“达摩院”这个名字也很马云。马云希望阿里巴巴的研究院也能像金庸小说里的达摩院那样,成为一个“武学殿堂”。这个殿堂的武艺,就是世界最厉害的技术。
因为它来得太天马行空,以至于有了“达摩院”的中文,才有了它的英文解释:“达摩”(DAMO)被拆解成了Discovery(发现)、Adventure(探险)、Momentum(势能)和Outlook(远见),涵盖了阿里巴巴的技术着力点。
2014 年夏天,从密歇根州立大学“停薪留职”来阿里巴巴做顾问的金榕,也第一次听到了“达摩院”这个名字。当时他已经在阿里妈妈做了半年顾问,主导完成了阿里妈妈广告推送机制的升级,通过优化推荐矩阵,将被动的推送改为提前推送,计算效率提升了30%。就在这时,阿里巴巴时任首席技术官王坚找到了他,希望他加入这个新成立的研究院,两人来了次“史上最短面试”。
“我们估计谈了不到五分钟。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定下来要我。”金榕回忆。王坚的问题很简单,他问金榕觉得要怎么做好大数据这事情。
“我的回答就是,做数据通常的做法是业务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技术人员把它抽象去解答,但是我觉得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业务人员可能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他看的东西比较短视。所以一个好的技术人员,很关键的不仅是知道如何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知道怎么找到正确的问题。”
听完金榕的回答,王坚就说了句“OK”。面试就算通过了。金榕之后正式加入了阿里巴巴。
像金榕一样,当时人工智能的人才大多在海外,所以达摩院的招聘目标也更多瞄准海归。“考虑到招的一堆人都是从美国回来的,而且初期大多只是研究算法,还不知道和业务如何连接,觉得这件事与达摩院的宏大想法相比还很小,所以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IDST(全称:数据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编者注),没敢用达摩院的名号。”刘湘雯对PingWest品玩回忆。
金榕加入IDST后,生活和工作都发生巨大变化。从在美国时每天泡在办公室不需跟人打交道的象牙塔生活,变成了兵荒马乱、天天需要和团队沟通的“战场”。一开始,他感到非常不适应。
金榕的第一个项目是给聚划算做个性化的搜索推荐,他发现,理论上十分完美的算法,到了现实中却因为完全不符合业务逻辑而失效了。
“他们的业务逻辑非常多,像选品、排期,一开始真的搞不懂他们在干嘛。然后他们也搞不懂我们在干嘛。每一次跟业务方开会,我说完头三句话,同事能说三个小时不停。每次都这样,我就插不上嘴了,光理解他那一段业务逻辑就要花很大时间,然后每一次逻辑还都不太一样。”金榕回忆。他没法把这些业务逻辑变成简单的数学,感到十分挫败。
与金榕一样“不适应”的还有同年加入的漆远,在此之前他是美国普渡大学计算机系和统计系终身副教授,被王坚等人打动后,回国加入阿里巴巴。但在他的第一个项目,为阿里巴巴平台设计“大规模机器学习平台”时,由于不善沟通,团队甚至一度到了解散的边缘。
关键时刻是井贤栋阻止了团队的解散。“他当时就说,你都研究这个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要解散。”漆远回忆。
这之后,漆远和团队开发的技术率先用在了阿里巴巴平台的广告功能上。真正上线后,内部开始看到不断增长的数据,他的团队终于得到认可。
金榕也终于度过了一年多的“挣扎期“,他开始理解业务,调整后的算法也终于发挥作用。尽管经历曲折,但他感到“一切都很值得”,因为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那些理论研究变成真实影响上亿人的功能。
这之后金榕带领团队开发了上传照片识别商品的拍立淘。“这是让我非常高兴的一段经历,因为每天将近有 2000 万人在用这个产品。”
在金榕们逐渐适应的同时,支撑马云最初那个关于“达摩院”的设想的外部条件日臻成熟, 2014 年 9 月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之后的财力也可以支持更大的计划,数据科学与技术研究院(IDST)也逐渐找到了一条前沿技术与业务场景互动的路径,更关键的是,阿里巴巴已在技术体系上已经有了足够的积累。
因此,真正的“达摩院”在马云的再三催促下, 2017 年底正式“挂牌”了,行癫出任院长。
达摩院从成立之初,就与过往的商业公司建立的研究院不同。它不是贝尔实验室那样天马行空但不接地气的研究院,也不是DeepMind或Google X那样短期内无法商业化或者针对某些特殊场景研发技术的研究院。它更像一个建立在各个具体业务部门的实验室,背后是阿里巴巴眼中技术与商业在未来可能的关系模式。它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灵活切换,成为一个非典型的商业研究院,但又正是典型的阿里巴巴风格。
“阿里以前最擅长的是把产品做成商品,后来我们也比较擅长把跟我们业务场景离的比较近的技术变成产品。比如云。但把基础技术转化为与产品离得比较近的那种原子型的技术时,以前阿里的家底是不够厚的。”刘湘雯说。
“这个阶段我们比较严肃讨论的,就是这个家底要做厚的问题。所以成立了达摩院。这其实决定了达摩院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做基础研究的机构。”
行癫以阿里巴巴CTO和阿里云总裁的身份来负责达摩院,也让达摩院的基础研究与阿里的业务结合的更加密切。对于那些能马上拿来用的技术,阿里强大的工程团队能帮助快速实现,而对于那些当下无法实现的研究,则可以交给达摩院的实验室负责。
以达摩院名义招来的许多科学家,加入阿里后同时成为阿里云某个技术事业部的负责人,比如在美国学界工作 15 年的犹他大学终身教授、数据库系统专家李飞飞,加入达摩院并负责阿里云数据库事业部;曾就职Facebook和Google,创建了深度学习框架Caffe的华人科学家贾扬清,加入达摩院,并负责阿里云大数据计算平台事业部。
行癫给这些科学家们也布置了严格的KPI,他对PingWest品玩介绍,阿里“投入上是有严格限制的,我们希望研究要解决的80%、90%还是技术问题,10%到20%是科学问题。因为科学问题到技术问题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并不希望现在大部分时间就去研究科学问题。”
“马老师一直强调达摩院以后一定要自负盈亏,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技术是有价值的,跟产业是能结合的。不然的话,跟大学搞研究所有什么区别呢。”行癫说。
这种“80 20”的结合,是一种产业思维和技术理想主义的结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2018 年 9 月达摩院旗下成立的芯片公司平头哥。它并非阿里巴巴突发奇想要秀芯片的肌肉,而是业务安全性和技术未来趋势的考量。
在业务逻辑上,行癫形容做芯片这件事,本质上和当年去IOE是一样的。他认为首先要真正把云技术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向部件深入,从最底层的技术上做到自主可控。其次,从未来的技术趋势上看,云平台和IOT平台的成功必须是靠“软硬结合”。
有了这样的业务逻辑,下一步要确定的是在芯片技术上与对手竞争的策略。行癫认为在摩尔定律失效的大背景下,想要芯片能力提升,就需要提供新的框架,或者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场景做专用的芯片。后者其实就是“弯道超车”——平头哥推出的基于RISC-V的芯片属于嵌入式芯片,它不是为了提供通用计算,而是要做一个行业的解决方案。
2019 年 7 月 25 日,平头哥正式发布了玄铁910(XuanTie910),这是目前业界性能最强的RISC-V处理器之一,可以用于设计制造高性能端上芯片,应用于5G、人工智能以及自动驾驶等领域。据阿里巴巴介绍,玄铁 910 的核心性能比目前业界最好的RISC-V处理器性能高40%以上。
紧接着, 8 月 29 日,平头哥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了基于玄铁CPU 的SoC芯片(系统级芯片)平台“无剑”。阿里巴巴将其定义为面向AIoT时代的一站式芯片设计平台,上面提供了芯片架构、基础软件、算法与开发工具的整体解决方案,希望帮助芯片设计企业降低一半的成本。
到 9 月 25 日在“云栖大会”上发布“含光800”,阿里巴巴已经基本建立起它的芯片布局:从终端处理器IP、终端芯片设计平台SoC到云端AI芯片,它希望“端上做芯片基础设施,云端为企业提供普惠算力”。
而在 2018 年的时点大举投入芯片并长期布局,阿里巴巴多少也被赋予了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它是整个中国推动芯片“自主研发”努力的重要部分。
就像阿里巴巴的“去IOE”一样,它起源于阿里巴巴对自身业务的危机感,但一旦真正实现,其意义便不只局限于阿里巴巴,而是掀起了整个中国信息产业的去IOE风暴。去IOE的成功实践,给整个中国云行业带来了全球话语权。
同样地,在前沿的AI芯片和智能物联网芯片组等领域,阿里巴巴的首要出发点是自身技术架构的需要,不过一旦取得突破,带动的可能是在下一代AI驱动的半导体研发、设计和制造领域,中国厂商和中国产业的全方位自主。只不过这个过程注定更加艰难。
达摩院希望解决像芯片技术自研这样的难题。最关键的是能否吸引来最顶尖的人才。阿里巴巴的方法是,不再“就事找人”,而是让这些科学家在阿里丰富的业务场景上,寻找他们最感兴趣的环节,提出他们的改进方案。
“我们不是找你来解决一个问题,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场景,希望你来发现问题,定义问题,”行癫说。
这是一场“双向选择”。科学家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需要得到阿里巴巴的认可,获得认可后,阿里巴巴作为互联网公司的灵活性就会体现出来,它会给这些科学家充足的授权和支持。
“平台给你了,公司对你提供支持,而你必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然后讲清楚的事情,就必须要去实现。”行癫对PingWest品玩说。
“原来他们只是搞研发,现在有了完成任务的压力,有指标,还要处理一些并不擅长的事情,比如怎么跟客户交流,怎么处理故障和运维。他们要平衡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是痛并快乐着。”
因为有理想主义,所以快乐;因为要现实主义的结果,所以痛。在理想主义的土壤上做现实主义的事,所以痛并快乐着。
离开待了 15 年的美国学界回国的李飞飞,在阿里巴巴的第一年里深切感知了行癫口中的痛与快乐。 “我在阿里巴巴没有自由,”李飞飞对PingWest品玩说。
“但这不是贬义词,”他补充道。“如果有人告诉你在公司里有自由,那这个人一定没有好好做事。”
李飞飞口中的自由,指的是美国高校普遍的宽松环境。“要说自由,肯定高校里最自由,你可以决定自己研究什么,哪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到了企业,就完全不一样。”
李飞飞在 2018 年加入达摩院,负责数据库的开发。他希望能看到自己研发的技术落地的一刻。因此失去学术圈那种“自由”的痛苦也可以忍受。
“如果我每天很痛苦我肯定早就走了,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在这待着。阿里吸引我留下的是它在研究与工程上的紧密结合。”他对PingWest品玩说。
“阿里有达摩院下的数据库实验室,同时也有阿里云数据库事业部的工程团队,两边可以打通。科研的东西可以反哺工程,工程的挑战也反哺科研。两个环扣在一起,不会脱节。全世界有这个条件的企业不多。”
但这些对李飞飞来说可以“忍受”的代价,对许多其他习惯了学界环境的技术明星来说则无法接受。PingWest品玩和李飞飞谈起和他同名的、著名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教授在Google云担任技术负责人的时期并不算十分顺畅的经历时,李飞飞做了个比喻:
“其实这就好比在沙漠里,明天就要渴死了,现在给你一杯水,你喝了也是死,但能多活一天。而这杯水还很脏,从技术的角度,你要给它烧热、净化,但这个过程就需要一天。有所谓技术洁癖的人,就宁可站着死,于是选择不喝,今天就死掉了。有些人对技术根本没有追求,他没有思考拿过来就喝了。”
“而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在技术上也有追求,但会选择先喝了,因为喝掉后还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阳,也许就有变化了呢?这样一天一天没准就能活过一年。”李飞飞说。显然,他就是这另外一群人。
对于许多学术界的人来说,能不能喝下那杯让你活一天的水,以及能否忍受喝下去的过程中伴随着的强KPI和加班熬夜的痛苦,就是区别的关键。
如行癫所说,阿里巴巴与这些科学家们一直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而在过去 10 年的人来人往中,继续留在阿里巴巴的工程师、科学家们,共同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技术文化。
这种文化强调技术具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双重性,要在现实中去践行理想,而非在理想中去构建现实。
这种文化源自阿里巴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使命。当技术还不足以对业务带来什么改变时,技术就是一个支撑部门;当技术已经开始制约自己的业务发展时,那无论如何也要改造技术;而当技术可以反过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时,那当然要大规模地投资技术工作者和科学家们。
只不过,这种强调“务实”的技术文化在过去 10 年与中国互联网界所推崇的“工程师文化”显得格格不入。后者强调自由,而阿里巴巴的技术文化显然也是一种大一统的文化,它也要受整个阿里巴巴的价值观指导。
阿里巴巴在商业上的成功似乎也成了它缺少工程师文化的佐证。在阿里巴巴要做云计算时,人们嘲笑马云不懂技术被忽悠;当阿里巴巴提出新的技术概念时,也会被贴上只会造概念的标签;即便阿里巴巴成立达摩院,也一样让外界怀疑,一个电商公司能做什么前沿研究。
这种“冲突”在 2016 年中秋节的“月饼事件”中一度达到高峰。
当年中秋,由于阿里巴巴内部发放的月饼备受欢迎,公司内部上线了一个预订页面,但 5 名安全部门工程师通过编写脚本代码,秒抢了 133 盒月饼。阿里巴巴很快开除了涉事的 5 人。
这个决定立刻引发舆论一片声讨。“这只是个恶作剧,何必上升到价值观层面”,“这个事情本质上就和把震动棒放到鼠标上一样”,各路评论纷纷指责阿里巴巴缺少工程师文化,阿里巴巴俨然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公司里的异类。
如今看来,那些对强KPI和集体意志十分抵触的人,很可能受不了阿里巴巴。但这更多是性格使然。还有很多批评者,则是习惯了耍小聪明而不愿思考技术真正价值的人们。他们理解的工程师文化,事实上更像一种投机取巧的精致利己主义。当你跟他谈价值观和责任,他自然会十分反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多在阿里巴巴游刃有余、如鱼得水的科学家,他们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力可以真正为人所用并创造价值。
这样看来,阿里巴巴确实没有这种“工程师文化”。某种程度上,阿里巴巴的技术文化更像一种“科学家文化”,它形成于一次次宏大的技术体系再造与重组中,它不局限于对某个单独产品的关注,而是从底层技术和基本架构出发,思考技术对商业的作用。它是一种更高级的技术文化。给它打上鲜明烙印的也从来不是工程师,而是两名前架构师王坚和行癫,以及越来越多的像贾扬清、李飞飞和金榕这样的科学家。
“阿里以前的文化叫做平凡人做非凡事,现在我们更强调的是非凡人做非凡事。我们相信会有更多优秀的人认同阿里文化,愿意加入阿里这个平台,消除书生气,做这样的转变。”行癫说。
外界对于阿里巴巴技术能力的看法也在改变。
自从 2012 年左右中国互联网出现BAT的叫法后,三家公司曾就被各自打上标签:“百度的技术,腾讯的产品,阿里的运营”。但当时间进入 2019 年,人们发现,百度迟迟无法从陆奇的离职中缓过劲来,技术研发路线几经重整,腾讯内外动辄陷入关于企业基因的玄学争论,纠结于toC的产品经验到底能不能帮助toB业务。
反而是阿里巴巴,其技术体系演进在过去 10 年并未出现什么大的中断,成为在技术积淀上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同时,它还建立了达摩院和成立平头哥这样面向基础科学的机构,有了自己面向未来的储备。
“因为云,人家觉得阿里巴巴好像是一家高科技公司,因为云的技术在输出了。然后我们做到部件、做到底层,大家的概念就更强了。阿里今天有CPU,有芯片,今天所有认知里不认为做软件是高科技公司,总觉得你做个硬件,做个手机,做个服务器,做个芯片,才是高科技公司。其实大型的软件更复杂,只是我们在云之前外界没能触达大家。”行癫对PingWest品玩说。
“所以我觉得阿里已经是家技术型的公司,高科技的公司,”行癫强调。
作为一家“碰巧成为互联网公司”的中国企业,阿里巴巴用它 20 年历史的一半时间完成了对自己的技术重塑,再造了自己,面向下个 20 年,它将蜕变成一家将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的更纯粹的科技企业。
这个过程将不再是“碰巧”,而是一种隐约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