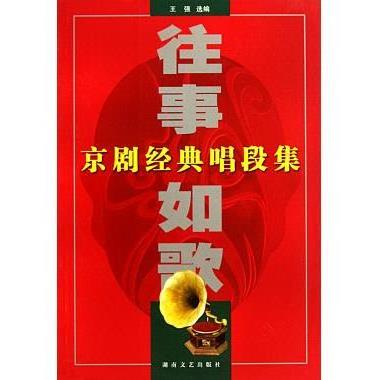京剧袁世海唱段 袁世海回忆录(85)演张飞 回味无穷
在剧中,我饰演前孙权、后张飞,饰演周瑜的是姜妙香先生。我出科这些年,无论在北平还是在上海演《龙风呈祥》,大都是盛兰饰周瑜,这次他已回北平,姜妙香先生正在上海,他听说我饰张飞,二话没说就同意饰演周瑜。我们没有在一起合作过这出戏,尤其是最后张飞要和周瑜交战,将周瑜挑下马来,为了不出纰漏,必须找姜妙香先生对对戏。我早早地到了后台,去姜六爷的化装室。

“大姨夫,您好!我请您说说后边的开打。”姜六爷已故的前夫人是福媛的大姨一一她母亲的胞姐。
“噢,小姑爷,我也正要找你哪,听说是你的张飞,我就放心了。二话没说,就把这个活儿接下来了。咱们外头吧,外头宽绰些。”姜六爷笑眯眯、慢声慢气地说。

“您甭忙,我的时间挺富余的…”
“不,不,不,早扮三光,晚扮三慌,咱们先对吧。走!”
他匆刻地系好靴带,未及换水衣子就随我走出化装室。人人都说姜六爷性格随和,在梨园界中是出了名的老好人,真是如此,一点儿脾气、架子都没有,谁和他相处都会产生好感。前几年,世芳去天津、济南演出,世玉正在外地搭别的班社演出,一时不能回平,只得特请姜六爷来承芳社饰演小生角色。

所演的一些梅派剧目,对与梅先生合作几十年的姜六爷来讲是轻车熟路,但《昆仑剑侠传》《金瓶女》等剧目是尚派戏,姜六爷没演过,由我来给姜六爷对词、说身段。那时我和福媛还没结婚,我们还没这层亲戚关系。

姜六爷十分谦虚,向我这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后生不耻下问,我很感动,又热情地介绍了一些应有的情感和表演。戏演得很圆满。事后姜六爷和夫人特在天津的小食堂请我吃饭。姜六爷原工青衣,后改小生,向冯慧林先生学戏,续娶了冯先生之女、毕业于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官称大师姐的冯金芙。
二人年岁虽相差较大,但夫妻感情甚好。那天吃饭时,姜六爷和夫人不住地夸我不光能把昆仑奴演好,还能把小生角色的窍头都说出来,真有心胸!也许这就是姜六爷听说我饰张飞就放心地答应演周瑜的缘故吧。
我们选中通往楼上化装室的楼梯前比较宽绰的通道,刚要对戏,见姜六爷双手一拱说:“五爷,您早啊!”我回身一看,盖叫天先生来了。
盖五爷身穿雪白的水衣子、大红彩,脚穿黑厚底靴、脸上也化好了装,眉间点着红眉心,这扮相使六十岁的盖五爷显得年轻、俊朗。今晚他饰赵云。他也双手一辑:“六爷,您在这儿对戏哪!世海,听说你已经回北平了,连良非要调你来不可,你是后生可畏呀!”说着一手拍在我的肩上。我笑了笑,没说话。盖五爷接着说:“这会儿的时间宝贵,你们说戏吧,我到楼上去找找梅老板,也是对戏。“
说着他一回头,朝后招了招手,我扭脸一看,是林三爷(林树森,饰刘备),他已换好水衣彩裤,只是没抹彩,他和我们打了个招呼,随盖五爷上楼了。
接着传来盖五爷的说话声:“梅老板,咱们得说说,我这个跑车”的“编辫子”可不太一样,别给您撞了!”
“好哇!您给我和林三哥说说……”
我和姜六爷这里也一边念着:“一合”“两合”,转身,跪下,蹉步……”一边走出步法,并用手比画着。就在姜六爷转身要下跪的时候,我突然有个想法。姜六爷虽是擅长文小生且唱功甚好,扎靠角色也演了许多,小时我看过姜六爷饰演《穆柯塞》中杨宗保等许多扎靠戏,手、眼、身、法、步都很帅的,但如今姜六爷毕竟已近六十岁,又扎靠又穿厚底靴,前边两个下场已经很累,到周瑜和张飞交战时,没必要再展示周瑜的武功,完全可以简化一些。
于是我说:“大姨夫,我看咱们是不是一枪?二枪您甭转身,我把您枪卸掉,往前一歪身,我就叫小张飞(随张飞上场的兵)过来将您捆绑了,您看好不好?”
“嘿!我不转身,省事多了。好,咱们再来一回。”
《龙凤呈祥》是过去演大合作义务戏常被选中的一出戏。因其剧名蕴含着吉样之意,适合在喜庆的场合演,更重要的是此乃一出群戏。无论是孙尚香、乔玄、刘备、吴国太、鲁肃、赵云、张飞,还是孙权、周瑜、贾化、乔福,每个角色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尤其诸名家分别在剧中饰演适合自己行当的角色,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家可以像一盘散沙似的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前輩们始终遵循着“一台无二戏”的宗旨,相互间均有些同场时的要求,所以,引出前辈们你找我对、我找你对,认真负责,团结合作的一段佳话。这种凝聚力,我以为是京剧兴盛、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些美德,我们后辈不仅应继承,而且应该进一步发扬,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我饰孙权下场后,重勾张飞的脸谱,要在平时,时间比较松快,这次可实实紧张,为的是挤出时间看盖五爷的赵云和几位的“跑车”。
我没有看过盖老的扎靠戏,曾闻盖五爷的扎靠戏也是极好的。早年,一位文武老生并擅演老旦的名家杨瑞亭演《八大锤》,年轻的盖老饰剧中的岳云。武打中,杨瑞亭先生左右两骗腿时,盖老扎靠在杨腿下左右两个鹞子翻身,靠旗唰唰两扫台毯,却不会碰到杨先生的腿。足见其靠功扎实。这次盖五爷饰赵云,又得扎靠,必须一睹为快。
盖五爷饰演的赵云完全继承老派,扮相很别致,我曾见过老前辈俞菊笙和陈德林老夫子演《长坂坡》中《投井》一场的剧照,盖老的打扮和那上面赵云的穿戴一样,头上打扎巾,用包头在左额系成慈菇叶。而且盖老饰演的赵云不起霸,只“待头”打上,在“九锤半”的锣鼓点儿中,左右手苦思,充分表现了赵云因刘备招亲后不思归故里而着急,很合情理。
“跑车”一场的“编辫子”,盖老身段多,圆场跑得圈大,如果孙尚香、车夫、刘备脚下功力差些就会显得笨拙,可是台上都不是寻常之辈,梅先生饰演的孙尚香边唱边跑,唱得是字字珠玑,跑得又稳又快,加上林树森先生饰演的刘备,三人按绞辫形往来穿梭,个个足下生风,引得观众掌声不落,叫好声此起彼伏。着实精彩!
该我这个张飞上场在芦花荡口迎候他们了。张飞这场走边只几分钟,此时,所有演员都要在上场门候场,就是饰乔玄的马先生也已经卸完装,换好便服在下场门等候谢幕。大家势必都会看我的表演,対我来讲,犹如一场考试。我鼓足了气,铆足了劲儿,干脆利索地表演了下来。
散戏后,全体演员到华茂饭店吃夜宵,扮演鲁肃的周信芳先生和我一同下楼。周先生看看我,笑了一下,说:“老弟,你演戏可真会讨俏!”论理,我比周先生晚一辈,他亲切地称我为“老弟”,表明他把我当自己人,甚至是门生弟子看待了。当时梨园中有这样的风气。
“他这场戏演得短、小、精、巧。”走在前边的梅兰芳先生听到周先生的话,回首笑着补充了一句。
得到梅先生、周先生的肯定,我当然打心眼儿里暗自高兴。这并非是自鸣得意,从前辈的肯定和鼓励中,我又悟出一个道理:我们的艺术必须要一代代地继承、创新,否则就会停滞不前。梅先生、周先生及其他前辈们从不故步自封、墨守成规。正是由于他们在虚心继承的前提下,不断改革创新,发扬光大,才创出各具独特风格的流派,推动了京剧艺术的繁荣。我的艺术之路,也应该这样走下去。
事隔三十几年后,我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住在香山饭店。一天,天空下着冰凌小雪。饭后雅兴,漫步曲径磴道,绕过层层叠叠的双峰驼石,又登上有如苍鹰欲飞的怪石。峰回路转,发现一人倚坐在石上。紧走几步细看,原来是曹禺同志,他正神韵潇洒地坐在那里休息。
看上去,曹禺同志面容略显清瘦,但目光锐利而深邃,身体很好。这位老剧作家的《雷雨》《日出》等名剧,我在三十年代第一次随尚小云先生去上海时就观看了,很受感动,可以说是他的剧迷。
简短寒暄后,曹禺同志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九八一年,纪念梅兰芳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演出《龙凤呈祥》,你饰张飞。我看了很有感触。在各地,这出戏我看过许多次,别人演的张飞场次比你多,还有的腰腿功也比你冲,为什么看了反而觉得平淡、拖,这是怎么个道理?你讲讲。“
曹禺同志提的这个问题可谓一语中的!这也是我几十年来一直琢磨的问题。
“您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是在《龙风呈祥》中我饰演张飞,《芦花荡》一场仅仅几分钟,嘁里喀喳,干脆麻利快,解决问题下场了。因为从剧情上讲已经不允许拖延,此时周瑜道杀刘备的主意已定,吳国太送给孙尚香的宝剑已失去作用,只要周瑜追上刘备,就会杀了他。
这当口,张飞上场,可以说是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也是最佳时刻。正是由于这样,张飞上场没两下子,观众看着不过瘾,不行,可是张飞若有四下子、五下子,多了,也不行。观众急着想知道周瑜追上刘备没有,不允许张飞在场上没结没完。这是就剧情而言。“
停顿了片刻,我又说:“另一方面,从演员来讲,今天演这出《龙凤呈祥》的演员,大都是小辈或平辈了,过去却是前辈占多数,不能让他们在后台紧等着,我必须上去得精彩,下来得痛快,这两种因素促使我加快了节奏。”
曹禺同志点了点头:“嗯,好,好!
“嗐,这出戏从我在科班里造魔算起,至今已演了五十余年啦!”
“五十多年的老陈底,都让您给掏出来啦!好,我就都抖搂抖搂。”
我们俩都笑了。
・美人计·回判州·芦花荡》。《回荆州》时就有张飞扎靠至芦花荡接刘备,一气周瑜;接着演昆曲《芦花荡》时,张飞再次去接刘备,二气周瑜。我觉得很不合理,但因前后两次张飞装束不同,唱的曲调不同,也无人深究。等我在科里能顶架子花脸的活儿了,胆子也大点儿啦,敢造魔了,演《回荆州》我就用昆曲《芦花荡》中张飞的渔夫装代替扎靠,借用了昆曲的“草履芒鞋渔夫装,豹头环眼气轩昂”几句定场诗和边挂子的动作,又加上“急急风”站门,私下和鼓师对好鼓点儿就硬着头皮上场了。
萧先生看了点头说不错。刚夸完,骆连师兄的昆曲《芦花荡》又上场了,这回可是完全重复了。萧先生站在上场门说:“呦!怎么又来啦!《回荆州》不是挺完整的戏了吗?!就别再唱昆曲《芦花荡》啦!从那时候起,因为有在富连成说活掷地有声的萧先生给开了绿灯,我的演法在科时就被大家接受了,直到今天我还这么演。“
曹禺同志说:“有意思。”
“另外我的表演与众不同,是因为我删了一场戏。有的人总以为场次多、事由多,才算得上剧中主要人物。我倒不这样看。观众喜欢不喜欢你演的人物,不在于场次多少,而在于戏精彩与否。《龙凤呈祥》中不管谁饰演孙尚香,演到与刘备洞房花烛夜,戏就已至高,《龙凤呈祥》了嘛!
这时的观众很惦记结亲后孙、刘的矛盾将如何发展,再回头表张飞担心刘备此去东吴会有危险,听到诸葛亮在帐中抚琴,闯帐质问,于是诸葛亮派张飞至芦花荡接应,就是画蛇添足。
这场戏名为《听琴闯帐》,简称《听琴》,如果这样演就使剧情出岔了。这场戏本想表现张飞鲁莽的性格,结果张飞却说“暂把怒气搁一旁“,又讲”未曾通报我不敢闯“,根本没有闯帐的莽劲儿,反而把张飞豪爽、急躁的性格淡化了,戏很平,同时把张飞《芦花荡》一折急急风’上场的气氛也给冲淡了……”
“所以删去!”曹禺同志说。
“我对这出戏的理解也有个过程。在科班,我常在演大义务戏时看名家们演这出戏。可是,每逢《听琴》一场,时常会有些观众“抽签”,到外边去抽烟或是上厕所,等赵云起霸才回来接着看戏,成了固定的休息时间了。当时不懂其中的道理,只是认为这场戏唱了白唱,不如不唱。
等我长大出科,搭马连良先生的班社,常演这出《甘露寺》。最初,马先生只要求我演与他同场的孙权,后来,又有意让我前饰孙权、后饰张飞,我欣然同意。为了便于赶场,《听琴》这场戏赶不及,我又有在科班时那种演了白演的印象,就果断删去了。不过,真正想清楚其中的道理,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你对这出戏的理解,时间跨度很大哟!”
“可能就是得有反复实践的过程才成吧。”我感到坐的时间长了,有些凉意。
“边走边说吧!”我站起来,说道。
“好的!”
“五十年代初,有一次演这出戏,领导要求我演《听琴》,我照令执行,结果令人遗憾!《芦花荡》从来是掌声迎上送下、火火爆爆的一场戏,那次完全被拖沓的节奏给破坏了。由此,我才开始冷静地分析应不应该要《听琴》这场戏,也才进一步理解了当年梅大师评论其“短、小、精、巧”的深刻含义。”
“听了你这番讲解,我又有一种感觉。”曹禺同志略低头沉吟了一下,抬头望着我说,“现在的演员还有你这种不断琢磨的劲头儿没有?我看得打个问号。”
当然了,这些都是一己之见,绝无强求之意。艺术应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非常喜爱这出戏,这出戏伴随我度过了六十多年的舞台生活。直至七十六岁时,我每日练功还要将这场戏的功架拉一遍,不是要老展雄威,而是挚爱至深,不肯释手罢了。
有着几十年交谊的老友、红学家冯其庸同志,四十年代在上海天舞台观看过我演张飞。一九八六年,又在上海天蟾舞台看我演此剧,见当年与我同台演出饰主要角色的诸前辈、平辈们均已作古,不胜感慨,我也是心结难平,稀嘘之余,题诗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