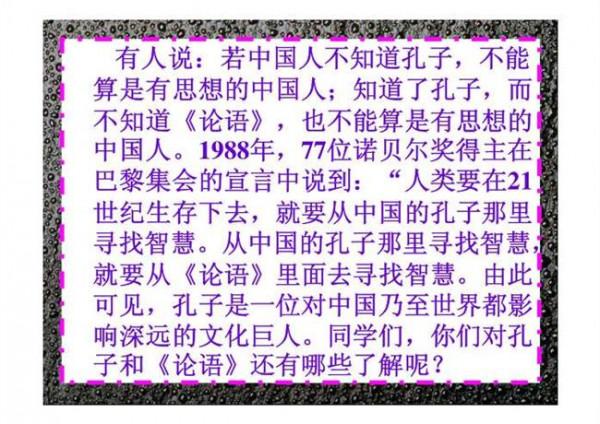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学而时习之 不亦乐乎
人言读书苦,其因在于世人以“书”为工具去追求外在物质利益,而非以读书本身为乐事也;予言读书乐,乐在精神充实与丰沛,乐在生命的润泽与境界之提升。孔子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乃成人之学,以充实自己为主旨,故学乃乐事也;为人之学,则是以“炫耀于人”而学,炫耀之事,耗神费力,虽有炫耀后的虚荣心之满足,但时时充满伪装、机心而缺乏“云无心而出岫”的自然洒脱,自然是苦差事也。

更何况,其虚荣心未必因学而得到满足呢!
当然,予以读书为乐事乃深受《论语》之影响。愚以为,某种程度上,《论语》乃中华民族之《圣经》,鉴于历代大师辈出,粗陋若吾等小子者难以对《论语》做整体评判,遑论研究?不过,若就《论语》中影响吾辈之最深切者,莫若《论语》开篇之语。窃以为,开篇之句虽寥寥数语,然言简意赅,一语道尽圣人“乐学”之本怀:非但为我华夏子孙治学之境界,亦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人生之取向。请备述之。

《论语》开篇之语,世人耳熟目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②]
孔门弟子以此句作为开篇之语,可谓深得孔子精髓。孔子一生以学为主,按夫子自道,自其十五而志于学,其后无论为鲁国司寇还是于“仓惶然如丧家之犬”的颠簸流离之时,总是“卷”不离手,“诗”不离口,世人由此有俏皮话孔夫子搬家——少不得书(输)。

及至晚年仍钻研《易经》,“假吾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说明孔子晚年至少在五十岁之后又在钻研一门“新学问”——《易经》,全然不类世人所谓“人过四十不学艺”之说。
若谈及孔子求学之途径,可谓广矣!除了求学于经典外,亦向各种人士学习,如孔子曾问礼于老聃,学琴于师襄,问政于郯子,即便在流离失所之途中亦不忘求学于渔父、农人。孔子可谓“终身学习”之典范,这一点亦为夫子欣慰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论语?公治长》)后世之所以将夫子首先以大教育家称之,就在于其“一以贯之”的“学”之精神,《论语》中“学”字竟出现凡六十五次之多,可谓证据确凿!
孔子酷爱学习,其缘由何在?答案在于“不亦乐乎”。在孔子视域下,学习本身乃是一种快乐,夫子对此深有体会:“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尔?”(《论云?述而》)更何况,动物亦能学,“学而时习之”中“习(習)”之古义乃表示人向鸟类学习(習从羽从白),《三字经》云:“人不学,不如物”,人焉能不如物?当然,人与物的最大差别在于动物之学乃靠生存“本能”所“逼迫”而不得不学,而人则靠其主动性去学,以此提高人之德性、智慧,并从中获得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快乐。
而只有在“学”中方可渐悟万物之理,体悟生命之流行,方可达到孔子所推崇的“中庸”境界,获得“至乐”。无疑,这种快乐是超越物质享受之上的大境界。孔子曾这样评论其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颜回之所以能安贫乐道,就在于其在“学”中体悟到大乐。不过,此种体“道”之快乐,非有“一以贯之”的学之精神不可!对于“乐学”之义,也许今天并非至难之事,只要把学习当做修身之目的即可。
然而,遗憾的是世人往往将学习作为获取某种功利的工具、手段,结果造成了“为学”之异化。于是“乐学”亦随之蜕变为“苦学”。非但如此,后人甚至还对子夏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做了“篡改”,子夏之其本意是“学习有了余力则可以从政(“从政”何尝不是一种实践性的学习?),从政有余力则要学习”,凸显的仍是其师孔子的一个“学”字。
而当下人们将之解读为“学习优秀了去当官”,当官“风光”了再利用其“手腕”去获取更高的文凭,于是才有“硕士、博士高官”满天飞,而学问却不见长的怪现象发生。若子夏重生,不知做何感想!
孔子重视“学”固然因为学中有“大乐”,然此“大乐”并非意味着经过一次简单的学习即能体味到,而是在反复的“习”研、咂摸中,方可体悟出些味道:此即“学而时习之”中的“时习”之要义。
关于“时习”有两解:一为时时刻刻“不间断”义,即孔子所谓的“一以贯之”学习精神(在今天可理解为终身学习之理念)。《中庸》中记载孔子所言:“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意指即便人们学了关乎“中庸之道”的知识,也很难坚守一个月,若能做到象颜回那样三月不违“仁”,已经少而又少了。
孔子的意思是,学了一种知识后,要“守死善道”,时时习研之、实践之,而不可如“过耳东风”、朝三暮四。孔子特别欣赏颜回的“时习”精神:“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中庸》)“时时刻刻”沉浸于“道学”之中,偶有所得,便紧紧抓住唯恐失去,此非有痴迷精神不可。只有沉浸其中不为外物所动时,关闭外在诱惑,“苦”才有可能转化为“大乐”矣。
佛教之净土宗亦提倡“时习之”的“不间断”功夫,”如《弥陀经》言,若佛弟子,口诵佛号,应时时不断,“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乱”,定能修得正果,得无上大喜乐。道家亦如斯:“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道德经?十六》),一“极”,一“笃”,亦是用心一也,不间断之义。可见“时习“之功夫,亦是上乘功夫,否则,儒释道三家何以皆重视之?
“时习”另一义则为“经常”义,即要不断的复习、回味之、践行之。“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这里的“温故”亦可理解为经常对学过的东西进行反思、温习。由于人们受阅历、经验所限,故学到的知识往往是未经体悟的“表层语言”,而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即便原来看似简单的“知识”也会变得丰满起来而转化为“内在的智慧”——转识成智。
这种对知识看法的转变颇似禅宗的“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渐次提升、挖掘、修炼磨砺之过程。更何况古人之学乃德性之学,若缺乏体悟、习练之功夫,知识终究是“外在”的。
这样看来,“时习”既包含了“一以贯之”的终身学习之理念,亦蕴含了对所学知识的温习、巩固乃至以阅历、经验以及反思的“渗入”而渐次达成“转识成智”之过程。高明的老师固然要传授“既定”的“知识”,更要进行“智慧”的启迪,“学而时习之”即涵盖了“转识成智”的智慧提升之过程,也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孔子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的道理。
对于“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后儒理解得颇为到位,无论宋儒所推崇的“孔颜寻乐处”还是明儒王心斋所谓的“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见《明儒学案?泰州学案》)皆抓住了“乐学”之核心。
对于学之目的则莫若张载说的清晰:“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朱子近思录》)。当今之时,世人虽有读书者,然以读书求乐者少,以读书变化气质者犹少。人们似乎被外在的东西所“俘获”,忘却了“人之为人”应给具有的更重要的东西。也许,在这各充满喧嚣的世界理,我们要回到孔子,重新感悟并倾听孔子的声音:“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