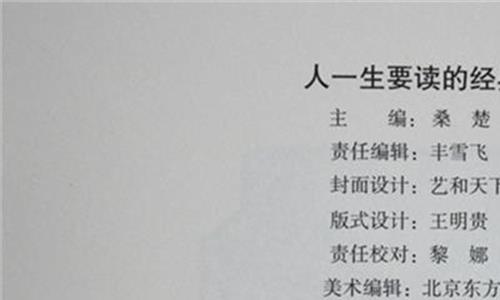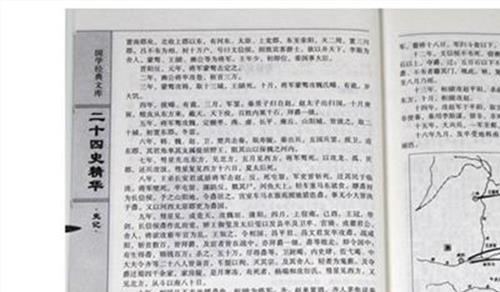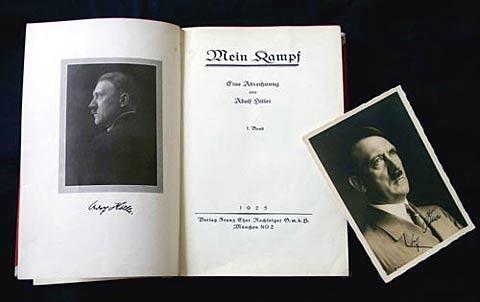止庵惜别 止庵:《惜别》在线阅读
二〇〇二年,母亲自己买了一套房子,待装修好入住,已是转年头上,她整整八十岁。这可以说是她晚年最大的一件事。将近二十年前,她在日记里一再写道:
“什么时候,我能有一间北屋,有大玻璃窗,让阳光普照在我的花上,清清静静地度过晚年。”
“这么破的小房子,怎么能收拾干净,我做梦都希望有间像样的房子,什么时候才有呢?”
“我总幻想有一个较好的环境,过着平静安适的生活。”
“我只在幻想,希望有一天一套房子落在我的头上,白日做梦,结果一天一天拖下来,还住在这间阴湿的房屋里。”
最终可以说她是在现实的意义上实现了弗吉尼亚?吴尔夫讲的“自己的一间屋”了。母亲给姐姐写信说:
“我又和小沙说,学校说给我钱购房,实在是太晚了,我都快八十岁了,所以我把新房装修好了,我自己住住,自在几年,以后如何再说。小沙也理解我的心情,他与别人说学校给这钱只是对我妈妈心理起了一点平衡作用,过去二十多年所受的苦,那是无法补偿的,青春年华一去而难返。我也和他们说,我能活下来已经是很不错了。”
“这个家我得来不易,花了不少心血,又有多少舍不得的物件,期望能在这里多待些日子。”
她在那里住了四年半,生病了;又过了三年,病重住院,再没回来。这段时间总共占她一生不到十分之一。
母亲在写给姐姐的信里记录了装修房子的过程:
“在装修前我们要看材料,要心中有打算,如何装修得好而又不化那么多的钱,我们还要去别人家看看,多听意见,不要忙,反正房子已买下了,又不是那么等着住,要吸取方方这里装的不足地方,别着急,装好改起来就麻烦。”
“你对装修的意见很可取,我们不会装成宾馆似的。阳台顶上有现成的架子,如那个阳台晾衣服就安两根横的铝合金的长杆,可将衣架挂上。我不喜欢客厅外的阳台晾衣服,到了那边也是厨房的阳台晾衣服,客厅与主卧室不晾衣服,我多在做完晚饭后才晾衣服,第二天就干了,不愿意挂得乱七八糟的。”
“过一两天我们就去看材料,离我们近处就有两家建材市场,很全的。多看几家,比比价钱、货色。我可不愿意买太次的料。”
“搞装修的张建来了,我们先去离我们住的地方较近的正时家居,我已经几年没去建材市场了。这正时家居面积不小,跑来跑去,挑材料。好的材料太多了,你都不知道光磁砖有多少种,当年方方装修时可没那么多,而且他装的磁砖已没有了。
装修建材进展很多,看得你眼花缭乱,也不知哪种好。反正我们看上的都是价高的,当然由于钱不多,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要求,中等即成。我们挑了厨房砖,很淡的绿色。我的卧室刷成淡淡的粉色,小间是淡黄色,使屋里更温馨些。”
“洗脸盆现在都时兴一个玻璃脸盆(各色)放在台面上,我想不要那么时新,还是看好一个椭圆形的,镶在大理石台面内,下面是柜子,可以放洗手间用具,这样外面不乱。墙上是一面长方形的大镜子,很大的,上面有射灯,这是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非常大气。”
“本来在卧室一角,我准备做一小柜,可以坐。都说不如买一把椅子,又舒服,还美观,说那一排大柜还不够放的吗?想想也是,椅子比较灵活,可以搬来搬去,不一定非坐在那角落里啊。装修不断地更改,日趋完善,真费劲。”
“去了玉泉营建材市场,说好了有三米长的防火板,到了那铺子又没有了,介绍材料上的我们看上,问仓库又没有,反正把我们烦得要命。最后还是按照我当初的设想,橱柜门是深色的,台面是浅的(最初被方方和小张否定,可最后还是按我的意见)。防火板是无法要了,只有两米四的,不够长就要接,有缝,容易进水,防火板怕水泡,会走形,改成了人造大理石的,这样又要增加九百元的造价,不过漂亮些,贵也只能贵了。”
“装修基本到了尾声,主要这主卧室的壁柜麻烦,到底什么柜门,我想想百叶也不好看,脏了很麻烦,光板又不好看,最好是与房门差不多的,还是漆成白色。研究来研究去,总怕做出来不好看。我们现在是请装修的木匠做的,如果买现成的门,那就顺利多了,又漂亮,但价高多了。所以说省钱就得多费力、费时,也属无奈。”
“买了主、客卫的镜子、不锈钢马桶刷、卫生纸架,等等,又去买厨房及鞋柜的把手(花样繁多,要选),又去订了暖气片外的铁艺。暖气的热气要把墙熏变色,所以要在上面挡一挡,暖气正面是铁艺,让热气散出。上面是块大理石面,没有暖气时可以放些摆设。两间卧室及客厅的铁艺是黑色的,厨房的是白色的,因为厨柜门是深色的。”
“我时不时要过去新房看看,哪些地方差点,可以指出。”
母亲提到的正时家居,在她生前也已经被拆掉了。那时母亲午睡醒了,我常陪她去那里,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一直转到该做晚饭时才回来。
母亲在搬入新居那天的信中写道:
“搬家可把大家累坏了。早上九点半吴环就来了。我在先已把衣物都放在手提包或大的塑料袋内,大大小小好多件,加上我床头的小茶几,由方方和吴环陆续搬过去。小张和木匠说好,中午吃完饭来,都说不用搬家公司,由他们用他那工具车就可搬去,他的车后备箱可通前座,经常装装修的材料。
中午由我做了油菜虾米龙须面,吴环特爱吃,再配了几样小菜,就解决了中午的饭。然后就搬大件,小张他们搬了三次,把我屋里的床,梳妆台,小柜,老虎椅,落地灯,台灯,还有原放在阳台上的玻璃茶几和两把藤椅,都搬过去了。
最难搬的是我那大电视,特沉,还有老虎椅,到了我那房子,还是把卧室门拆下才放进去。我的衣物还有好些没能搬过去,以后慢慢搬。我是最后去的。
吴环把搬过去的家具先擦了一遍,把我的屋子收拾好,她坐在我的老虎椅上,看那宽阔的卧室,舒服得不想起来。都说我的卧室太好了,主要是带阳台,还有一个大卫生间可专用。八十岁的我真是享福了。当然比上不足,但比一般人就非常满意了,很知足。”
母亲曾写信告诉姐姐:
“我这房子最好的一点就是冬日来临,还是热热乎乎的,在太阳好时,更是晒得暖洋洋的。……我小时候在天津所住的洋房,二楼有阳光的南向的房间是我父母住,他们屋里除了向南的窗子还有两扇向东的窗。这房子还连着洗手间,有两个门,一通他们屋子,一通过道。
我的屋子是向西的,而且窗户是对着旁边那家的墙,中间隔着一条小巷。我的住房旁是用人房子,他们有个小厕所。还有一个门可以上到三楼,是晒台,有一间堆东西的房子。我两个弟弟住的屋子是向北的,不过有多扇向东的窗。
还有一间与我父母住的房间一样大,是小客厅,但前面有向南的阳台。鸿孙在那里照‘太阳灯’(我想是紫外线,因为要戴上墨镜)。我们的阳台窗下都是柜子,上开盖,可以坐,我们的玩具和小人书、书等都放在里面,到现在宋阿姨还记得这些柜子。
这阳台是突出的,现在都叫飘窗(我现在的房子的小卧室就是飘窗,报上登了以后不再盖这种飘窗,因造价太贵)。一楼有书房、客厅、餐厅,有进大门的大厅,楼梯上下时可以看见大厅,上面放了花盆。
还有厨房,用人的住房,吃饭的屋子。有一个小后花园,有葡萄架,有夏天可乘凉的座位,睡莲池三个角种了花,一个角可放桌椅休息的。这个房子是我父亲亲自设计的。父亲会设计,母亲会布置,所以我住在那里那么舒服,我终身不忘。
那时我们都很小,印象中房子很大。后来我去过那里,没进屋,但觉得不大了。小时候去过二伯伯在青岛的房子,也觉得房间多,院子大极了,可后来我随学校去青岛旅游,找到那里,就觉得不那么大了。孩子的眼光和成年的眼光有不同,但我的印象那么深刻。”
在这封信里,还配了几张插图。
母亲去世后,我在她的房子里继续住了一年。这一年我具体是怎么过的,回想起来有点像“真空地带”,虽然刚刚过去不久。我有如生活在母亲的废墟之上。或者说,我就是她的废墟。
在北村薰著《漂逝的纸偶》中读到一段话:
“千波的母亲是在医院去世的,不过她在这张床上躺了很长时间。床上的旧垫子已经拿掉,床架还留着,现在千波每天躺在上面,和母亲看到的是同一个屋顶。”
仍然存在的环境,在存在的与不存在的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延续性--我现在之所见就是她曾经之所见,我此刻的感受就是她当时的感受。这与“去年今日此门中”的诗中所写尚且有所不同-那里“人面”仅仅是作为被观察、被感受的客体而存在的。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那房子里听到楼上传来的持久的吵闹声--小孩们总是跑来跑去,每天清晨和深夜都拖动家具,仿佛那一家人难得安宁似的。母亲曾经很为这种噪音所苦,写信对姐姐说:
“过去战争期间,学生都闹着没有一个安静地方可以放一张书桌,现在虽是和平时期,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放一张安静的床了。”
“我有一个愿望 :等红星胡同拆迁拿回点钱,我要去外地或者北京市住几天大的饭店,安静的睡一觉,不要像现在总被人吵醒。我倒不是非去什么国家旅游,我就想美美地睡一觉,自然醒。”
如今这感受存在,这感受的对象存在,而感受者却已经不存在了。此种情况,殊不能令我理解,令我接受。走过小区,走过附近街上,见到种种熟悉景色,同样使我产生类似想法。
母亲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
每当想起这一点,仿佛觉得有另外一个时空,母亲,我,过去的生活,都在那里。它与现在这个只剩下我自己的时空之间,似乎不是先后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当我置身街头,野外,陌生的地方,往往没来由地感觉正面对着那个时空,就像遥远之处有一阵风吹过,或一片云飘过似的。
而现在这个时空里,就只剩下我的“母亲曾经存在”的念头了。
曾经存在--给人的感觉恍惚迷离,好像隔着一层厚玻璃似的东西,努力想看见一点什么。我记起巴勃罗?聂鲁达在《马楚?比楚高峰》中所写的:“从空旷到空旷,像一张未捕物的网,……”我说的这种“存在”,与仍然记得--记得清清楚楚--的她的神态,声音,动作,还不是一回事。应该更确切,更实在。
我独自待在家里,有时怅然想到:曾经存在,难道真的就是彻底消失了么。我素不相信什么“特异功能”,但假若有那样一副眼光,能在这空虚之中看见母亲过去留下的身影,就好了。














![郭生白本能论在线阅读 [转载]《本能论》郭生白著](https://pic.bilezu.com/upload/6/49/649ea03bd6c8c1dc65df9e73702e6e40_thumb.jpg)